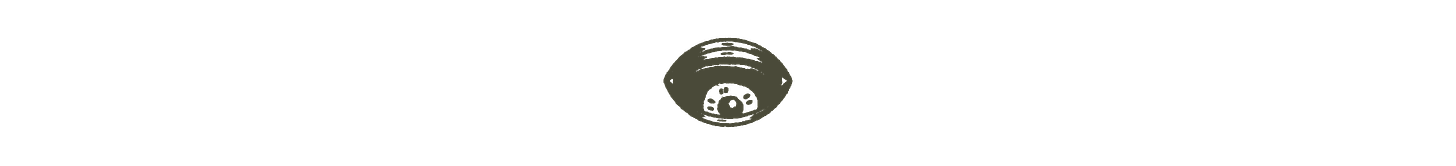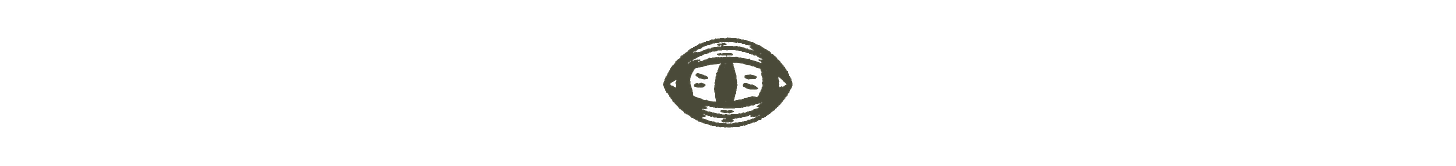最近,Karen 模因以一种非常真实的方式在我的生活中体现出来,其形式是追车,然后是警方的报告。
看,我通常和我的狗,德国牧羊犬密涅瓦一起把垃圾带到垃圾场。这是我们的许多仪式之一,让她坐在乘客座位上,把头伸出窗外,她很喜欢。这辆车又旧又臭,几乎只用于这个目的,垃圾场就在不远处。今年夏天,我做了一次这样的旅行,在回家的路上停在当地的一个小市场。我进去的时候把 Minerva 留在了我的车里,拿了六包啤酒,立即在收银台付款(从来没有任何线路),然后走了出去。在我进入商店的那一刻,一位大约 45 岁的白人女性来到了我的车旁。当我走近时,她开始责备我(她的感叹词更多,我重复的次数更多,所以这并不完全是逐字记录,但很接近):
凯伦:你怎么了?这是虐待动物!
我:你在说什么?
凯伦:如果你再次把你的狗留在热车里,我会找到你并报警。你是个施虐者。
我:外面只有80度。在我进去之前,空调一直在爆破,所以车很酷。我只在那里呆了一分钟。而且,窗户是向下的。看看我的狗。她完全没问题。 [我的狗坐在车里,窗户朝下,面无表情]。
凯伦: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我:汽车不只是在车窗关闭的情况下随机超快升温。我们没有处于创纪录的热浪或任何情况下,我们正处于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微风拂面。你不能因为某个人在夏天把他们的动物放在外面而生气。
凯伦:你是一个虐待动物的人。我要打电话给警察,他们要逮捕你。
我:我非常了解我的狗,她总是在更热的天气里去海滩,在 80 年代低的一天,微风吹着,坐在一辆停着的车里,窗户朝下,一分钟完全没问题,而且她的危险绝对为零。
凯伦:我要报警了。他们要把你的狗从你身边带走。
我:做吧,凯伦。让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
凯伦:你他妈的小婊子。叫我“凯伦”。去你的!
如果我尝试,我无法弥补一个宇宙的讽刺,在她对我尖叫的时候,我们对面是另一辆停着的车,车窗朝下,我向上帝伸出手,里面有两只德国牧羊犬,他们的舌头懒洋洋地搭在门边上。我注意到他们进来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品种,并且对自己说这是巧合。业主现在正从我刚来的同一家店里走出来。凯伦似乎没有看到,但车主看着我,我只能用痛苦的同情来形容。
我上了我的车(由于空调已经打开,车内的温度仍然明显低于外面的空气),然后开始开车。她急忙跑到她的车上,在路上肆无忌惮地追着我,尾随我。当我开始回家时,她继续跟着我,显然想知道我住在哪里。我把车停在一条土路上,这样她就不会发现了,她迅速将车滑过马路入口,挡住了我,让我无法逃脱。她下了车,继续对我尖叫。
凯伦:操你!我要报警了。
我:好!给他们打电话!把他们带到这里,凯伦。
这时,凯伦似乎意识到她犯了一个错误。她开着机动车追了我,然后把车停在车流中间,想把我困在某个地方。如果她打电话给警察,他们肯定会问:为什么你的车以如此疯狂的危险方式停在这条街上的入口/出口?你为什么追这个人?所以,在对我又尖叫了几声之后,她走上前,拍了一张我的车牌照片,尖叫着“知道了!”离开时轮胎发出刺耳的声音。
我确定她会报警,所以一旦我回到家(确保我没有被跟踪),我也这样做了。我打电话给部门号码,告诉他们这件事,我的故事,关于她鲁莽驾驶的事情,他们告诉我警察会给我回电话。他很快就做到了。
显然,发生的事情是该女子冲到警察局亲自报案。拿走它的警察就是我说话的那个人。命中注定,他是一名 K9 军官。当她告诉他这个故事时,他说他一直在等她到我做错事的地方。他向她解释说他和德国牧羊犬一起工作,今天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热,微风很好,温度是 80 度,她没有证据表明汽车温度异常,她承认窗户一直都关着,听起来我只是短暂地进入室内,而且这只狗没有任何明显的痛苦,因此没有危险。他不相信她无法理解这没关系,他实际上向我道歉。她还在警方报告中正式报告说我称她为“凯伦”。警察间接暗示(同时仍然保持对专业精神的合理否认),该站从警方报告中包含的凯伦指控中得到了很好的笑声。他告诉我不要担心,我的故事已经记录下来供后人使用。我们聊了一会儿德国牧羊犬的工作线来结束谈话,因为密涅瓦的父亲是一只训练有素的炸弹狗。
(我不应该说,但我会因为这是互联网:我爱我的狗胜过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家人之外的任何其他东西。她睡在我的床上,我努力不只是保证她的安全健康,但每天都通过郊游、飞盘、跑步、海滩参观、游泳和远足来丰富她的生活。她从来没有处于危险之中,这个女人对温度的基本知识感到完全困惑,狗和生物学。她情绪激动,甚至无法正确识别狗,因为她显然一直在向警察强调我有一只长毛德国牧羊犬,但密涅瓦是一只短毛德国牧羊犬。)
这一切都可能完全不同。我本来可以发脾气的。她本可以把她的车撞到我的。幸运的是,我碰巧知道如何与警察交谈,如何清晰地表达自己,以及如何保持冷静,而不是因为我在大学里担任紧急医疗技术员多年(我经常与警察一起工作)而使紧急情况升级。所有这些关于我背景的随机事实使我能够以轻微的事件(汽车追逐除外)度过难关。除了称她为凯伦之外,我从未升级这种情况。就我而言,这样做是非常有目的的。强迫某人说出“他称我为凯伦!”警方报告将报告等同于哥德尔句子:一个自相矛盾的陈述,就像臭名昭著的“这句话是不真实的”。我知道警方会知道,任何主要抱怨之一是“我被称为凯伦”的报告都不值得认真对待。
我也知道我随意使用凯伦模因可能会伤害一些人。我是第一个说将陈规定型行为附加到一个共同的名字或人口统计(如中年白人女性)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很同情,并希望模因以某种方式有所不同。虽然任何性别或人口统计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凯伦人,但我的凯伦人确实拥有模因中的确切发型。
因此,尽管我对将负面模因与特定人口统计数据联系起来存有疑虑,但我想说的是,凯伦模因具有必要且重要的功能,特别是因为美国文化深处的天真。因为美国文化最缺乏的是成年人对邪恶动机的理解。美国的邪恶概念始终是好人对抗坏人的幼稚观念。但这不是邪恶。邪恶实际上是什么,大多数情况下,善是腐败的。
在美国文化的现代神话中,它的电影中,“坏人”公开而自豪地作恶。星球大战中的皇帝。伏地魔。索伦。有时动机是权力或金钱,但即使在好莱坞的坏人除了坏之外还有其他原因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似乎很喜欢这个角色。甚至不要让我开始看漫威电影。
想想美国最基本的神话制造者:迪士尼。在标准的迪斯尼电影中,有一些明显很糟糕的主角(疤痕、贾法尔、加斯顿、厄休拉、邪恶的女王,字面上是哈迪斯),他们将自己插入主角的生活,以某种方式委屈他们,而主角反过来总是阻止作恶者计划的反作用力。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敌人都会在迪斯尼电影的结尾意外死亡。他们都滑倒了。即使辛巴让他出局,刀疤还是摔倒了。加斯顿从屋顶上失去平衡。邪恶的女王被闪电击中并从岩石上掉下来。
唯一一个足以杀死对手的迪斯尼角色是小美人鱼中的王子埃里克(Eric),他驾驶一艘船头破损的船直接进入厄休拉的肚子(这一切都是为了将爱丽儿从一定的死亡中拯救出来,因为厄休拉咯咯笑着说:“真爱! ”),但即便如此,如果是他的转向还是仅仅是一场事故,场景还是模棱两可的。迪斯尼不愿用灰色阴影作画,这是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Richard Hofstadter) 著名的美国政治“偏执风格”的早期幼稚形式。
现在将迪士尼电影与吉卜力工作室电影(日本迪士尼)进行比较。吉卜力工作室的电影完全不同。最常见的情节涉及两个交战派系,他们都有自我激励和不同的世界观。在幽灵公主中,森林精灵和钢铁镇之间的冲突是一个技术甚至社会进步的村庄(比如让女性担任重要角色并照顾麻风病人)。铁镇那边,有乌波希夫人,这一切进步的原因;森林之灵这边,我们有狼女森。双方在某些方面都表现出同情,而主角阿席达卡的目标是防止事态升级。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城镇和森林学会并肩生活的再生画面。
即使是吉卜力工作室团队的第一部电影,鲜为人知的《风之谷》 ,也具有相同的结构。在没有明确派系的吉卜力工作室电影中,比如千与千寻,对手比迪斯尼更有同情心。就像No-Face一样,黑色的幽灵面具人追逐并试图吃掉年轻的主角森,最终却成为她的朋友和盟友。吉卜力电影中的主角们通过他们的魅力和看到两面的能力走上了自己的路。我强烈认为吉卜力工作室的电影比迪士尼电影更接近世界运作的真相,尽管两者都是针对儿童的。
美国迪斯尼式的文化发展为我们偏执的政治风格,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假设大多数作恶的人都是虐待狂。当然,虐待狂确实存在。他们代表了最典型的恶人。在街角随意殴打老太太的人。杰弗里·达默。校园枪手。作为虐待狂,这些人开始制造痛苦和暴力。它通常带有性心理成分,通常是男性。在青年时期,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可能是由于缺乏认知发展——高中欺凌者和刻薄的女孩在一定程度上往往是虐待狂。但大多数人从中成长,只涉足虐待狂,真正的成年虐待狂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统计数据支持这一点——绝大多数暴力犯罪是由一小部分人犯下的。但虐待狂在媒体中的比例过高,因为很容易看出他们有多坏。将其与实际的历史现实进行比较,即大多数邪恶是由最好描述为道德主义者而不是虐待狂的人造成的。
以下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高峰时期指挥官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的话,他命令超过 200 万人进入不是淋浴间的淋浴间,然后将他们的尸体化为烟雾升空。
根据我目前的知识,我今天可以清楚地、严厉地、痛苦地看到,我如此坚定和坚定不移地相信的整个世界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前提之上的,总有一天会彻底崩溃。所以我为这种意识形态服务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尽管我坚信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没有人想听到这个,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个忏悔。霍斯的童年是这样描述的:
他的父亲是一名前军官,曾在德属东非服役,经营茶和咖啡生意。他以严格的宗教原则和军事纪律抚养儿子长大,并决定让他成为神职人员。霍斯从小就对责任在道德生活中的核心作用抱有近乎狂热的信念。
像任何历史人物一样,有多种观点;也许鲁道夫·霍斯确实是一个虐待狂——一些报道称他为冷酷和反社会的人,而这种行为当然是他所做的事情所必需的。这当然是更舒适的位置。但我认为他很可能真的认为自己做得很好,而且他父亲期望他成为一名牧师并不是什么奇怪的历史巧合。换句话说,他是一个道德家。
我不是,我再说一遍,不是说鲁道夫·霍斯是个好人。他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人之一。我是说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做了他所做的,承担了其他人不会做出的“艰难选择”,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很难理解,但当时的纳粹并没有将犹太人视为受害者。相反,犹太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安排德国屈辱的“压迫者”。当然,纳粹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只是被他们自己的种族主义激怒了,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的行动是因为相信他们是与坏人作战的好失败者。
但是,拜托,纳粹显然不是坏人吗?单单从他们的深色制服来看,对吧?有些人的头盔上甚至还有头骨!都是真的。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二战中肯定也有很多头骨图像,而且他们是好人。双方有时穿着灰色,有时穿着绿色。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电影中看到过绿色的纳粹和灰色的海军陆战队,不是吗?
这听起来很陈词滥调,但不知何故被遗忘了,没有人愿意在胸前挂上“我是邪恶的”的牌子。人们喜欢对希特勒爱狗而且是素食者的事实视而不见,事实上,他会用屠宰动物的照片来纠缠他的晚餐同伴,以劝阻他们不要吃肉,认为这是不必要的痛苦。直到今天,德国的虐待动物法与纳粹最初通过的法律相同。这并不是希特勒和纳粹之间矛盾的一面。反过来说——希特勒强烈的道德感是他播下邪恶的原因,他关于杀死“坏人”和不吃肉的信念在他看来从不矛盾。事实上,它们源于他心理学的完全相同的方面。所有的纳粹高层都是邪恶的种族主义者,但我认为大多数都是邪恶的种族主义者,不是因为他们是虐待狂,而是因为他们是道德家,要找人责备,并且在确定了一群他们认为是坏人的人之后,确实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可怕事情。对于那些定义了我童年的恐怖分子,那些驾驶飞机冲进双子塔的人,我愿意说同样的话。他们也认为自己做得很好。他们是道德家。
我们可以暂时假装是颅相学家,并想象道德是人类大脑的一个特定模块,一个自成一体的灰质块。道德家是指道德过度发达的人。拥有如此过度的道德感几乎是你登上飞机杀死自己和成千上万其他人的唯一途径。没有人这样做是为了享受虐待狂的乐趣,正如我们可能希望相信的那样。仔细分析,我相信即使是最卑鄙的人物,如斯大林和波尔布特,至少在他们早期的动机中也是道德主义者,如果他们真的成为虐待狂,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有必要实现他们的道德愿景。
考虑一下英国帝国主义的例子,它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罪恶。但当时不是。事实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化得到了当时主要的道德哲学家的支持,例如早期的功利主义者詹姆斯·米尔,他以功利主义的理由为殖民主义辩护。虽然有些人可能会指出像普京这样的现代恶棍,但当普京就他入侵乌克兰的原因发表演讲时,他们完全集中在西方(普京认为的)腐败、霸权、压迫和侵略上。
尽管这个真理的本质是狡猾的,但道德主义是邪恶根源的知识就像一条矿石矿脉在西方文化中流淌,一遍又一遍地被重新发现。即使是最神秘和最隐喻的。就像在托尔金的神话中一样,兽人是堕落的精灵。或者就像在基督教中每个魔鬼都曾经是天使一样。或者阿纳金·天行者,这样的典范,成为达斯·维达的呱呱叫的光头。
就我个人而言,我很久以前就不再相信红色或蓝色光剑了。主要是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和经历生活。几乎所有冤枉我的人都普遍认为他们做得对,见鬼,即使是中学欺凌者也可能有他们的借口和自己的观点。当我搞砸了时,我通常认为我做得很好,结果我对什么是“好”是错误的。从这些教训中,我的光剑现在将成为《星球大战》经典中的中立部队用户所使用的:灰色——那些在部队中寻求平衡的人。这是和平缔造者的角色,他意识到没有人真正获胜的妥协是对抗那些想要支配他人的人最重要的力量。实用主义者、政策专家、外交官、具有多种观点的作家、吉卜力工作室、对美比政治更感兴趣的艺术家、移情者、和平主义者、权力下放爱好者、过度关注其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地方主义者、嬉皮士只想独处而不被干扰的公社——都是灰色的光剑。
克伦迷因,以它自己的小方式,提供了对道德主义邪恶的防御。作为一个模因,它是一个脆弱的盾牌,只适用于特定类型的事件(对于道德主义,我希望我已经明确表示,这当然不是中年白人女性独有的)。但这个模因至少指出,对世界情节的自我感叹往往有害而不是帮助。
当然,Karen meme 有时会以特别美国的方式来解释,暗示 Karen 之所以是 Karen-ing,是因为他们是虐待狂。他们想与经理交谈,因为他们想让员工的生活变得悲惨。这可能偶尔会发生。但我认为,凯伦人的道德裂片往往偏大,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能看到邪恶的阴影,并不知疲倦地努力将其根除,即使邪恶只是办公桌后面一个反应迟钝的员工,应该做他们的工作并帮助人们,而是动不动就与克伦人作对。每当光剑在好莱坞嗡嗡作响时,无论是蓝色还是红色,都会诞生一个凯伦。
当我的私人凯伦在她的车里追我时,我能感觉到她的仇恨正在沸腾。在那一刻,她会很高兴地看着我死去——事实上,她愿意用她鲁莽的驾驶来危及我和我的狗。她被自己的道德确定性所控制,寻找不公正的东西,她已经准备好看到她不禁看到。就像所有迫切渴望让世界变得更加公正的人一样,她对某种恶魔附身有着独特的开放态度。世界的真实历史就是这些恶魔来来去去,一边战斗,一边战斗,而历史的车轮仍然顽固地对最常见的邪恶来源是善的智慧视而不见。
原文: https://erikhoel.substack.com/p/karens-and-the-nature-of-ev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