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 1860 年左右的某个时候,一个名叫雅各布·夏普的人站在曼哈顿钱伯斯街和百老汇的交叉口,数着公共汽车的数量。据他计算,每 15 秒就有一个,或者在 13 小时内超过 6,000 个。每辆公共汽车——一辆可以载十几个人的马车——速度快、不舒服,而且有利可图。但夏普知道他可以做得更好。通过计算交通量,他可以向纽约市议会提出他的理由,他们应该让他在马路中间铺设铁轨。通过用钢轨上的钢轮代替鹅卵石上的木轮,同样的马可以在火车上拉更多的乘客。这意味着街道更有序,马粪更少,路线更规则,骑行更顺畅。他是对的:铺设了铁轨,最终马被蒸汽机取代,然后是电力。
但即使有轨电车的迅速崛起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初,汽车也出现了。它无法证明社会效率和改善公共安全——它带来了无情的屠杀,导致成千上万的人(主要是儿童)死在街上,因为新的驾驶者努力理解亨利福特赋予他们的这种新权力。尽管如此,它将超越有轨电车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交通技术,将建筑环境重塑为对其自身看似不可避免的证明。
汽车将建筑环境重塑为对其自身必然性的证明
最初,汽车受到了谴责。 大约一个世纪前,定期游行公开哀悼汽车的生命损失,汽车被视为富人的致命玩具。许多城市制定了法律,要求所有汽车都配备限速器,以维持街道上的秩序。尽管有这种阻力,汽车公司还是能够组织汽车俱乐部和政府游说团体,不仅可以对抗反汽车情绪,还可以动用数百万美元的公共资金来建设扩大汽车使用所需的基础设施。到 20 世纪中叶,艾森豪威尔政府承诺建设一个只允许机动车通行的国家公路系统。二十年来,汽车从令人厌恶到人类自由和安全,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汽车的出现导致了汽车文化——并非不可避免,而是通过对诱导需求、游说、基础设施变革、强制和最终路径依赖的协调。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使汽车对城市和人民不利的因素使其成为本世纪中叶美国企业的完美商品。汽车需要对城市进行彻底改造,为土地投机、房地产开发、建设和建筑改造提供机会。汽车需要不断的维护,因此为零部件、加油站、停车场和车库创造了全新的产业。保险、法律、工程和城市规划等领域出现了全新的领域。所有提取原材料并将其转化为燃料、零部件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公司也可以从中获利。这是对社会的物质、经济和文化基础的彻底重组,企业领导人知道,如果他们能早日进入,他们就能在美国帝国的顶端站稳脚跟。
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转变是多么微妙和心理。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会对从个人对城市的心理地图到自然世界的商品化等方方面面产生连锁反应。例如,在他 1991 年出版的《自然大都会》一书中,历史学家威廉·克罗农描述了 19 世纪中叶出现的一个问题,因为农业生产开始超过交通系统的容纳能力。如此多的谷物从中西部的农场运到芝加哥的谷物升降机,以至于他们无处可放。在那之前,“运输网络一直在努力维护 [that] Farmer Smith 的爱荷华州小麦永远不会与 Farmer Jones 的伊利诺伊州小麦混合,直到最终客户购买了两者”,这意味着谷物必须存放在单独的箱子中。当谷物升降机运营商在芝加哥贸易委员会的帮助下废除了这种做法时,它不仅简化了农业的商品化,而且还为通过电报新连接到中西部市场的东海岸银行对未来谷物价格的投机开辟了道路电线。
这一三步举措——从Farmer Smith 的黑麦到普通黑麦价格,再到未来以现在设定的价格购买黑麦的合同——将在汽车道路的开发中重复。首先是我家门前的路。然后一般为城市道路制定标准工程规范。最后,还有基于未来道路改善的土地投机。在每个阶段,新兴的交通技术都会将事物原样转化为金融资产的“基本面”。
科技借用了交通行业的底层商业模式:路径依赖
可以肯定的是,房地产投机也是有轨电车发展的核心,而不仅仅是汽车。金融家和地方官员认识到,附近城镇之间的便捷交通可以很容易地将景观变成一个繁华的大都市,而这些线路旁边的土地将非常有利可图。当旧金山著名的有轨电车首次上线时,根据Fares Please!中的 John Anderson Miller 的说法,Nob Hill 和 Embarcadero 的房产价值一夜之间翻了一番。但投机优先于社会效率也为有轨电车的过时铺平了道路。
现在这种模式再次出现。只是这一次,引发新的投机可能性的技术变革不是人们如何从这里到那里的工程改进问题,而是侵入性跟踪设备和不透明算法在百年老汽车设计中的机会主义应用。美国的交通系统正在“更新以保持不变”(借用 Wendy HK Chun 的一句话),以确认旧的特权并保护郊区的相同利益和意识形态投资。但它决定的不仅仅是土地使用模式:我们的个人主义交通网络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对投机、金融化和贪婪消费主义的根本性和永久更新的依赖。
巴黎马克思的无处可去之路:硅谷与移动的未来追溯了汽车制造商接管北美大陆与科技行业当前垄断力量之间的历史回响,“想让我们依赖他们的产品,而不仅仅是当我们浏览网页,但当我们也在我们的社区时。”部分原因是直接采用了早期的交通模式:通过监控和控制交通系统,Alphabet 子公司 Waymo、特斯拉和优步等公司可以暗示自己成为房地产开发商、购房者和其他任何人的数据经纪人想更多地了解或控制谁去哪里和做什么。这些信息可以输入新的提取方法(例如动态定价、访问控制、自动功能的订阅要求等)以及可以更快、更精确地适应的新的房地产投机和操纵系统(例如自动化住房市场)到不断变化的条件。从你如何工作到你的住房成本可以永久调整多少,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回报,而不是人类需求或集体福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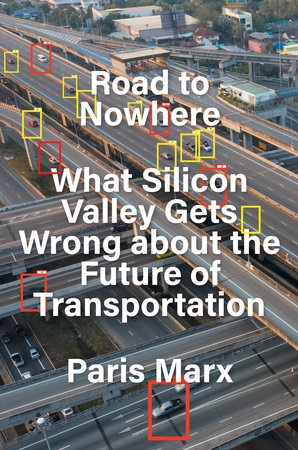
但科技不仅仅介入交通运输领域;它还借用了其潜在的创新:路径依赖作为一种商业模式。马克思的书的前半部分简要介绍了汽车公司如何在 20 世纪创造汽车文化,如上所述。尽管遭到了基层的强烈反对,美国汽车制造商还是设法说服政府投入前所未有的资金来扩建道路、修建高速公路并确保充足的停车位。这些论点听起来应该很熟悉,因为它们强调个人消费者便利对集体福利的压倒一切的价值随着对既定社会模式的每次新“破坏”而反复出现。
这种将便利视为美国生活缩影的框架变得自圆其说。汽车文化作为脱节的人民意志的自然表达而出现。 “随着汽车游说团体的力量增加,”马克思写道,“规划者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将街道视为一个市场,他们的角色是响应需求——他们认为需要的是更多的汽车空间,所以这就是他们提供的便利。”
马克思将这段历史与计算机行业的历史相提并论,并以类似的方式重塑社会形象。 1980 年,史蒂夫·乔布斯甚至将个人电脑与汽车进行了直接比较,称它“为个人提供了动力”,就像汽车在一个世纪前所做的那样。与汽车公司一样,微软、IBM 等公司能够在压制竞争对手的同时说服政府补贴他们所需的基础设施:政府拥有的网络架构和基础研究被出售给电信公司,重新分配来自公众信任的财富为私人利益。就像政府赞助建设公路网络时考虑汽车制造商(而不是公众利益或安全)一样,它赞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考虑的是科技公司,而不是哪种网络最能为公民服务.
这两个时刻预示着它们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组合,以削减企业权力:在技术创新的支持下,土地贪婪的汽车可以与数据饥渴的网络融合在一起,这被认为在超越文化规范和公共政策。如果这样的事态发展引发混乱,因为拼车公司挤满了街道,破坏了公共交通选择,半自动驾驶汽车杀死了行人,那又如何呢?进步的代价。
政府在考虑汽车制造商的情况下赞助了道路网络的建设
这种蓄势待发的危机使监管机构处于被动地位,迫使他们在竞争的资本主义部门和日益被剥夺权利的公众之间进行政治分类。人们甚至可以将其称为行政国家的小丑理论:资本家播下混乱,除了不断重申自己的主导地位的能力之外,对“新常态”没有任何特别的计划,而“反对派”则逐渐减少为弱者努力将客户与最坏的外部性隔离开来,并追溯使达到目标所需的一切合法化。犯罪行为被重新融入创新。
科技公司将其视为“创新”的使命,将尽可能多的事物、地点和人员置于他们的监管之下。有时这意味着将不显眼的传感器嵌入到奢华的商品和有趣的小玩意中;其他时候,这意味着强制重新开发世界,使其与他们的利润流更加兼容,就像汽车公司在 20 世纪不可逆转地改变环境以适应他们的产品,或者当科技公司如此公然和彻底地侵犯我们的隐私时,我们的规范在 21 日发生了变化。
最新一轮的颠覆利用汽车行业造成的负面外部性,向公众和政府兜售一系列新谎言:自动驾驶汽车、地下隧道、电动汽车和一群无人机可以缓解僵局(而且僵局本身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机器学习的魔力,高效地在车辆和街道上安排行程和全视传感器套件套件,汽车将变得更安全、更可靠,最重要的是,再次方便。
现实情况是,这是一场土地掠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动驾驶依赖于维护良好的道路标记和标志,而在紧缩的美国景观中无法提供。如果自动驾驶汽车要超越他们在西南地区的小型试点项目,他们将需要更严格的行人控制系统,通过硬屏障和自动门禁系统将汽车和人分开。它可能还需要将通行权移交给运营这些运输系统的公司——就像夏普的铁路公司和早期的电信公司如 MCI、Worldcom 和地区贝尔为他们的需求而获得的一样——这样他们就可以拥有更多地控制标牌和道路标记,这将必然面向机器视觉。 (想象一下点缀着数百万个二维码的开放道路的辉煌。)
如此多的新交通技术预设并强化了郊区土地利用模式。马克思认识到,“汽车的问题不仅在于为其提供动力的燃料,还在于公司和政府成功地围绕汽车重新定位我们的整个生活的方式,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已经淘汰了更有效的替代品。”对汽车有利的景观——在最终目的地有许多不透水的光滑表面和汽车存放处——使得其他所有类型的交通工具都更难以实施,因为一切和每个人都过于分散。
新技术,即使它似乎是朝着更好的道路迈出的一步,也受到这些遗产的制约并受到它们的束缚。考虑电动汽车的充电:即使充电时间可以从目前所需的几个小时缩短,它们仍然需要在汽车停放的任何地方。也就是说,它们仍然需要被认为方便才能可行。在人们被迫到处开车的郊区环境中,充足的停车位可能会使这种改造变得繁琐但易于管理。但在城市环境中,自动取款机大小的充电器最终可能会占用路边停车位旁边不断缩小的人行道空间。或者它可能会驱使电动汽车车主放弃城市,而权威人士则宣称城市生活是不可持续的。
在这一点上,乐观主义者可能会注意到,许多科技公司正试图推动人们远离汽车所有权,转向汽车共享安排,这将减少道路上和停车位上的汽车总量。但是这样的系统总是伴随着大量的监视来制定不透明的用户协议中内置的不民主且通常是任意的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对交通等基本服务的访问伴随着持续的监控和支付,类似于我之前所描述的订阅城市:应用程序和服务决定了您可以在哪里以及何时可以到达的条件。它突出了新型便捷访问的承诺,例如租用您原本买不起的完美面试装备,同时赋予突然且无可争议的禁令的新威胁,就像许多美国州在算法时对那些接受政府食品援助的人所做的那样决定他们不再有资格。将便利扩展到一个人群的监视也可以同时动员起来反对另一个人群,以排除他们。随着科技公司开始利用其垄断地位,我们可以预期监控的双重性质将成为其核心特征:根据谁能负担得起不断上涨的租金来组织世界。
运输部门是展示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部署的一个很好的镜头。人和物的移动被视为投机投资机会的先决条件,人们的生活、欲望和规范被重新定位以适应和证明这些转变。但是你只能把人们推到这么远,直到世界的形状必须改变以容纳所有的人,以及我们所有的希望和欲望。
在投机社区:在金融化世界中生活不确定性中,社会学家 Aris Komporozos-Athanasiou 开发了一种解决这种新兴状况的概念方法。他的“投机社区”理念是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社区”概念的更新,他声称这一概念出现于 19 世纪后期随着大众印刷媒体(报纸、小说)的兴起,并培养了共同的归属感到全国人口。在 21 世纪,算法社交媒体的兴起产生了一种不同的归属感,一种基于不同信息环境的投机社区。 Komporozos-Athanasiou 建议,与想象中的社区不同,后者由静态文本结合在一起,用于创造共享经验和文化,投机社区帮助人们适应社会存在如何从属于投机兴趣——即“路径依赖”和上述诱导需求。
“投机想象”有助于理解一个充满恶意的世界
完全可以预见,星巴克和其他连锁店将与工会作斗争,科技公司将收集数据并定位广告,信用机构将加剧收入不平等,但究竟为什么或如何发生这些事情还需要猜测。这为一种抵抗创造了机会。社会条件所产生的“投机想象”有助于理解一个世界的意义,这个世界的恶意可以毫不留情地预测,但它的内部运作却被掩盖了。
投机社区的其中一个工具是 Komporozos-Athanasiou 所说的“真正的假货”(他说,这是他下一本书的主题),他将其定义为“进步的反投机政治萌芽的地方”。投机社区使用协作的、阴谋论式的思维方式——真正的假货——来一起收集和处理信息,并发展他们自己的反叙事,从中产生某种意义。
例如,当快递公司用空运无人机或人行道机器人取代零工时,可能是他们试图降低成本和直接依赖人工。但无人机也可以被解释为间谍,一种无证搜查的手段,因此成为共享推测结论的政治基础。由于科技公司拒绝透露他们的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这种模糊性可以被当作一个政治机会来建立新的抵抗联盟。
因此,Komporozos-Athanasiou 认为,投机可以被理解为“我们通过它表达我们对新自由主义正在减弱的合法性的集体怀疑的白话”。真正的假货将“警惕自由民主和新民粹主义的虚假,因为它们对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脆弱性持开放态度。”也就是说,真正的赝品首先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可以解释世界为何如此运作,而忽略围绕各种实践而引发的不透明和怀疑的迷雾。
新自由主义转向社会和市场逻辑(如技术和汽车文化的融合)更完美的融合,这意味着信息——特别是知识产权和公司的内部运作——由于竞争原因变得更加模糊。这为投机创造了肥沃的土壤:不仅是关于社会将走向何方,而是关于权力如何试图让我们到达那里。他们发布了诸如The Great Reset 之类的听起来很吓人的计划,如果您不愿意购买 Alex Jones 类型的产品,那么几乎没有决定性的方法来理解这一切。
一些投机社区显然是反社会的,例如当 QAnon 编织半真半假、彻头彻尾的谎言和主流媒体对时事的报道时,会制造出一种没有方向的反动愤怒。 Gamergate 举了一个感觉很古老但还不到 10 年的例子,抓住了有关视频游戏制作的谣言和八卦,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女权主义文化反弹。虽然游戏行业正在以好的和坏的方式发生变化——在公司整合中开发游戏的人多样化——真正的假货是将这些变化解读为对年轻人的尖锐仇杀。
但“真假”的概念也可以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政治,尤其是考虑到现在霸权意识形态(“汽车文化”;“科技文化”)是从这种“假”中稳步建立起来的。普通人的投机想象力可以用来鼓励团结互助,而不是恐惧和偏执狂吗?
这是一个大问题,很少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叙事激增,许多大规模抗议的时刻来来去去,却没有持续有效地朝着共同目标迈进的政治活动。尽管马克思和 Komporozos-Athanasiou 的著作进行了有效的诊断,但他们大多忽略了有组织的劳工将我们面临的问题去个体化并将其转化为集体谈判目标的潜力。在近代历史上,没有其他机构能够有效地管理群众的投机力量,共同努力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
在不确定的时期,顺其自然是一种解脱:让公司和政治家做他们想做的事,并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有时,我们甚至可能以看似鲁莽的方式投票或投资,但与我们面前的严峻道路相比,其不利因素相形见绌。就我而言,我更愿意看到工人结合他们的力量,共同努力实现一个共同的、谨慎的目标。推测我们摆脱混乱的方式就像投降一样。团结我们讨价还价,分裂我们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