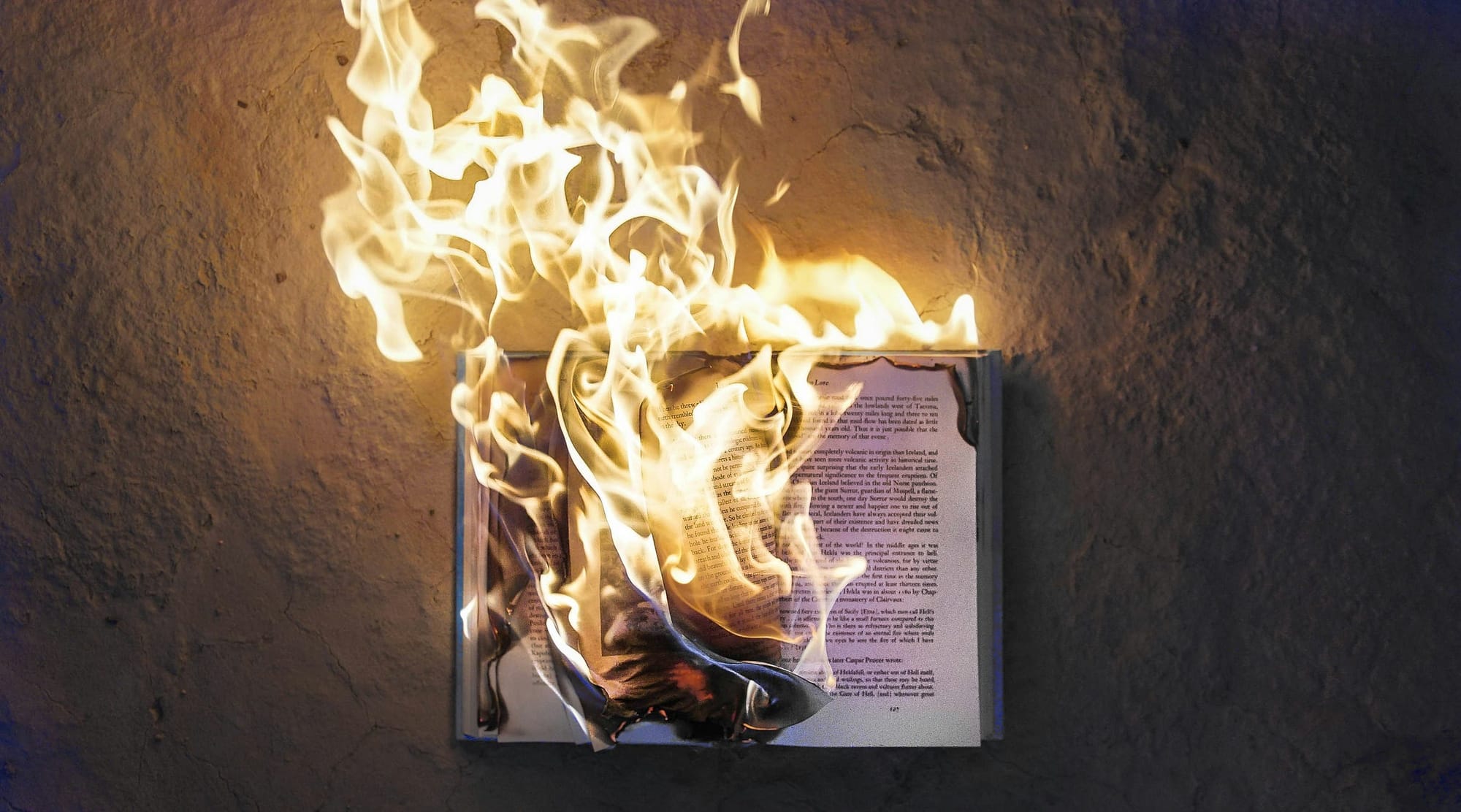
在一个小国家,你拥有对言论管制的完全控制权。您可以禁止所有有政治争议的言论,也可以允许完全的言论自由。选择权在你。
收获是什么?在知道哪个政治派别将在下个世纪掌权之前,你必须做出选择。
这本质上是约翰·罗尔斯*满足内容审核的要求,它说明了我们的首要原则:大多数人对言论自由的立场与他们目前是否拥有文化权力神秘地相关。
现代左派认为,不受限制的言论会助长极端主义。他们指出社交媒体如何放大激进内容,骚扰活动如何压制边缘化的声音,以及错误信息如何破坏民主话语。他们说:“你挥舞拳头的权利终止于我的鼻子,而你说话的权利终止于造成真正的伤害。”
现代右派反驳说,“言论控制”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思想控制”。他们提到了独裁政权如何通过限制言论来巩固权力。他们认为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糟糕的想法应该公开辩论,而不是被埋在地下溃烂。
他们都错了,但方式很有趣。
左派的错误是经验性的。尽管有人声称不受限制的言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极端主义,但证据充其量是好坏参半。言论法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例如,魏玛共和国对言论有重大限制(包括禁止侮辱宗教和鼓吹共产主义的法律),但这些并没有阻止其崩溃。与此同时,事实证明,拥有强大言论保护的国家对独裁运动具有极强的抵御能力。
但更重要的是,言论限制往往会适得其反。当法国禁止否认大屠杀时,它并没有减少反犹太主义——它只是让否认者成为烈士,并助长了阴谋论。史翠珊效应是真实存在的:试图压制言论往往会放大言论。
右派的错误是哲学上的。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言论限制可能是危险的控制工具,但随后却毫无根据地跳到“因此所有言论都应该不受限制”。这忽视了言论可以直接造成伤害——不仅是在拥挤的剧院里大喊“着火了”这样的极端情况,还包括故意协调骚扰活动、分享未经同意的亲密内容或煽动暴力。
这是一个更好的框架:只有当言论造成直接、可衡量的伤害且无法通过其他方式更好地解决时,才应对其进行限制。
这给了我们明确的原则:
- 限制言论的门槛应该极高
- 限制应针对具体的有害行为,而不是广泛类别的内容
- 限制应该是观点中立的
- 限制应尽可能精确以避免附带损害
在此框架下:
- 协调骚扰活动?限制
- 分享未经同意的亲密内容?限制
- 表达攻击性的政治观点?保护
- 做出与事实不符的主张?保护
完美吗?好吧,他妈的不。
人类则不然,等等。
这里有一个双方都忽略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言论自由辩论已经脱离了现实。我们争论社交媒体平台是否应该禁止极端分子,却忽略了大多数言论已经通过更微妙的手段得到有效控制:
- 经济压力(担心失去工作/客户)
- 社会压力(害怕被排斥)
- 算法管理(哪些内容被放大)
- 注意力市场(什么演讲甚至可以到达听众)
结果呢?我们名义上有言论自由,但通过软实力进行有效的言论控制。这个体系给了我们两全其美的结果——既没有右派想要的真正的思想市场,也没有左派想要的受保护的话语。
我们的语音框架的乌托邦改革可能看起来像这样:
- 对纯言论的极强保护
- 对特定有害行为进行明确、观点中立的限制
- 媒体/平台积极反垄断执法
- 公共空间(数字和物理)免受私人审查
- 对匿名言论的强有力保护
- 全民基本收入减少经济言论控制
这个框架将为我们提供比任何一方的提案更真正的言论自由。它将为异端观点创造空间,同时仍能防止具体伤害。当然,这意味着它不太可能出现。
核心见解是言论自由不是二元的——它不是“受限制的”或“不受限制的”。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仔细的机制设计。我们需要停止昨天的战斗,开始为明天建立更好的言论机构。
*在罗尔斯最初的思想实验中,他要求我们想象设计一个社会的规则和结构,而不知道我们将在那个社会中占据什么位置——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富有还是贫穷,强大还是边缘化,多数人或少数。我们的想法是,对我们未来地位的无知将导致我们制定更公平的规则,因为我们最终可能处于任何地位。
原文: https://www.joanwestenberg.com/the-left-and-right-are-both-wrong-about-free-spe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