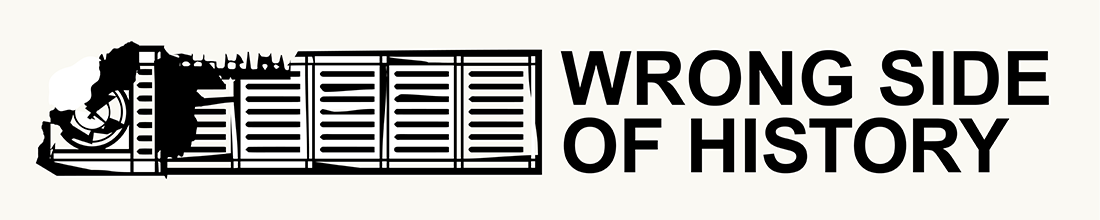每当我和家人讨论假期,解释为什么我不想花钱去昂贵的出国旅行时,我都会进入 Monty Python 的惯例,我解释说我童年的夏天通常会去爱尔兰呆上几周。渡轮——如果我们幸运的话! 我对爱尔兰的记忆是,它很穷,虽然我不知道它是否一定幸福,但它却非常安全。我和我的哥哥(大概 12 岁和 9 岁)早上会离开家,然后漫步进城,整天在 DART 上来回走动,或者在布雷海边的游戏厅闲逛。这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并不令人意外,因为 20世纪末的爱尔兰共和国可能是有史以来凶杀率最低的社会。在麻烦发生之前,北爱尔兰也许更加安全。 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上周在帕内尔广场发生的一名妇女和三名儿童持刀袭击事件就是最新的例证。随后发生在这座城市的骚乱以及政府的反应,既是欧洲管理不善的更广泛趋势的征兆,也是爱尔兰特有的从众问题的征兆。 作为一个在伦敦爱尔兰定居点大帕丁顿-尤斯顿弧区长大的塑料帕迪,我对我母亲的人民的印象是,他们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全国营销骗局。这个国家所描绘的形象是一种随心所欲、不守规矩的叛逆者,这是现代统治阶级假装庆祝的品质,但实际上他们是墨守成规的,这适合一个小岛屿社区。 这种误解部分是由于人们的群居性造成的。没有人真正知道为什么,但爱尔兰人拥有不同寻常的玩笑水平,这个词起源于近代早期的伦敦,但可能来自盖尔语,表示以有趣的方式交谈的能力。即使是爱尔兰人的中位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玩笑程度也排在第 90 % ,在芬兰等地则上升到第 99 % 。这在全球经济中尤其有利,该国的半地中海特征也是如此。爱尔兰的巨大优势在于它具有北欧水平的信任度和南欧水平的人际温暖(法国则相反)。但这种信任正在消失。 民族叛逆的神话源于英国几个世纪的统治。但爱尔兰人从来都不是天生的反叛者和违法者,他们只是从不接受外来种族的统治。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领导下,他们被证明是温顺的,首先是对埃蒙·德·瓦莱拉的保守天主教国家,现在是对取代它的革命秩序(并且蔑视它的继承)。 英国人普遍批评他们的邻居毫无疑问地服从神职人员,这种批评无缝地延续了世俗化和记者、政治家和非政府组织的更替,他们的思想痛苦地墨守成规,沉迷于象征道德价值和成熟;这是一个更广泛的欧洲问题,但在爱尔兰尤其普遍。 虽然喜欢开玩笑,但爱尔兰人在很多方面也相当沉默寡言,比英国人更沉默寡言,不太可能抱怨糟糕的服务或轻微的虐待,并且有一种“不能抱怨”的心态。这在大流行期间显而易见,当时该国经历了欧洲最长、最严格的封锁。 当爱尔兰十六世纪前接受基督教时,其皈依速度之快是不同寻常的。大多数国家经历了数十年的冲突,旧信仰与新信仰之间的文化战争,但爱尔兰人似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接受了圣帕特里克宗教,没有经过任何斗争。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新宗教身上,爱尔兰的精英们以极快的速度拥抱进步主义——也许只有加拿大能如此迅速地走得更远。 一个关键因素是国际主义。爱尔兰是欧亚世界边缘的一个小岛,常常具有全球视野。即使是最早的圣人之一的航海家圣布伦丹也因其探索世界的渴望而闻名。尽管爱尔兰在历史上同情英格兰的大陆敌人,但它主要是通过大英帝国表达其国际主义,特别是通过传教工作和为帝国及其统治的人民提供服务。我来自戈尔韦郡的叔叔是印度陆军的一名医生,他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 当我母亲长大的时候,爱尔兰教区会为耶稣会筹集资金来教育年轻的非洲人(包括年轻的罗伯特·穆加贝,谢谢)。随着鲍勃·格尔多夫(Bob Geldof)和波诺(Bono)等爱尔兰人试图消除全球贫困的积极行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代。 近年来,爱尔兰的国际主义表现出对欧盟的强烈认同感,这个新帝国对待这个国家比邻国好得多,让它以一种令我祖父母震惊的方式致富。但该组织的成员资格也让爱尔兰的精英有机会参与更大的事业,这对小国的统治者来说总是一种诱惑。 这助长了一种过度服从的心态,康纳·菲茨杰拉德曾将其称为“好孩子主义”。与此同时,爱尔兰的知识精英,即新的神职人员,完全受制于美国的文化主导地位,甚至爱尔兰的政治和文化都是在美国背景下构建的。英国也是如此,虽然这常常是不恰当的,但对于一个历史上非常同质的小国来说,不仅没有殖民主义历史,而且本身也被殖民,被视为从属的劣等种族,这几乎是滑稽的。 知识分子,有指导思想的知识精英,本身不是问题——只要他们明智、审慎,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然而,尽管现代西欧领导人痴迷于显得理性和成熟——最高的赞美是称一个国家“成熟”——但他们本质上也是革命性的。由于机构的激进化,他们认为合理且不可避免的想法实际上是极其极端的…… 订阅可以让您:
© 2023埃德·韦斯特 |
爱尔兰的叛乱问题
国家的危机源于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