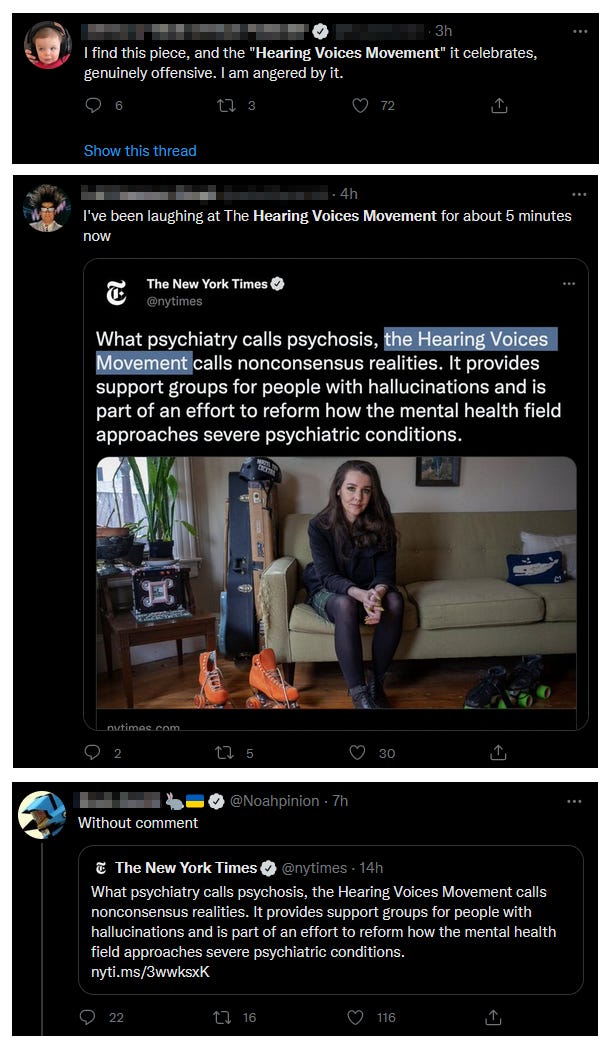1:
《纽约时报》发表 了一篇关于听力运动的文章——即有幻觉和妄想的人希望将其视为正常和正常的,而不是医疗化的。 Freddie deBoer在这里给出了非常热情的回应。其他人有不同的热情反应:
我遇到了一些听力之声的成员。我的印象是,这场讨论的每一方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好人,试图充分利用糟糕的情况(当然纽约时报的记者除外,他们是破坏美国的邪恶人物)。一些具体的想法:
2:
很多人都听到了声音。其中一些人是典型的无家可归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但很多人不是。我的一个病人是一位成功的计算机程序员,他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幻听。他意识到它们不是真的,尽力忽略它们,然后继续他成功的生活——就像他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做的那样。他因为无关的抑郁症来找我。
这家伙对他的朋友和同事隐瞒了他的病情。我完全不怪他做出这个选择。但是当每个可以隐藏它的人都这样做时,我们只会听到那些无法隐藏它的人,他们通常是最坏的情况。另外(就像一群 1980 年代的同性恋者可以告诉你的那样)对你认识的每个人隐藏一个关于你自己的基本事实很糟糕。
我向这个人推荐了听觉运动。我不记得他是否接受了我。但我认为让他可以谈论他的处境的人不会认为他疯了,或者试图把他关起来,这对他会有帮助。
3:
人们讨厌承认有些病例很轻微,有些病例很严重。尤其是在《纽约时报》工作的那种人
我在自闭症权利运动的背景下谈到了这一点。许多自闭症患者过着美好的生活,享受他们身体状况中有益的部分,但当精神科医生不断尝试给他们治疗时,他们会觉得这很烦人或令人压抑。许多其他自闭症患者无法生活在机构之外,并不断尝试咀嚼自己的身体部位。一个合理的结论可能是“第一组看起来很轻,应该单独处理,第二组看起来很严重,可能需要强化治疗”,但要让人们相信这一点却出奇地难。
称某些情况为“温和”听起来微不足道。将其他案件称为“严重”听起来是一种耻辱。无论您对轻度病例的标准是什么,都会有人符合这些标准,但说这种情况毁了他们的生活,而您正在消除他们的痛苦。无论您对严重病例的标准是什么,都会有人符合这些标准,但他们正在蓬勃发展并过着最好的生活,并指责您想 24-7 将他们监禁在医院里。
那只是激进分子!我们精神科医生从不同的方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看到了一些疯狂的@#!$。不管你的案子多么温和,我们见过一些乍一看像这样的案子,然后慢慢下降到恐怖电影的前提下。我们的本能自然是将每月使用一次 Xanax 的人变成终生吸毒者,将轻度抑郁的家庭主妇变成血腥的自杀受害者,将偶尔发声的人变成需要穿紧身衣的人。
尽管如此,有些病例是轻微的,有些病例是严重的。患有轻度精神病的人——比如我的病人程序员——可能不需要服用具有严重副作用的非常强效的药物。他们可能只是需要支持。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将在提供这种支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现实世界中,这些患者中的许多人都希望他们的精神科医生会发疯,过度用药,甚至可能将他们送进医院。这是现实世界,许多患者是对的。所以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4:
大致而言,社区对有需要的人有好处。
形成社区是困难的。一群无神论团体试图建立教会,但为无神论者。它通常不起作用。人们需要某种统一的因素。单独的无神论太无聊了,没有削减它。如果您非常渴望加入 KKK 或您所在大学的黑人学生联盟,Race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邪教证明,足够极端的信仰可以削减它。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足够多样化的种族身份或对我们thetans的各种化身的足够深入的洞察力,并且不得不摸索其他东西。
轻度精神病是一个体面的社区集结旗帜。幻觉是真的吗?可能不是,但上帝也不是,而且研究表明,如果你去教堂,你会更快乐。我希望参加听力运动会议的人也会更快乐。
建立社区的一种好方法是围绕迫害团结起来。大多数长期患有精神疾病的人都以某种方式受到精神系统的创伤。有时这是恶意或无情行为的特定个人。其他时候,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创伤,被一个没有优化的系统从一个机构拖到另一个机构,以防止你被困在轮床上十二个小时无事可做。
如果您想为最讨厌所有精神科护理提供者的人提供精神科护理,您可以做以下两件事之一。首先,你可以强迫他们——法庭命令、承诺、内疚等。其次,你可以非常强烈地表明你不像那些人。
关于听力运动的很多事情都令人畏缩。有很多关于你的“非共识现实”如何是好的,在某种意义上一切都是真实的,以及如果你看到天使或其他什么那么美丽,你必须是一个深刻的精神的人。
我认为这些说法是错误的,但这正是重点:它们是没有自尊心的精神病医生会说的那种话。这意味着它们是很好的信号,表明该运动不仅仅是精神病学机构的另一个分支。这意味着患有慢性精神病的人实际上可以在那里感到安全并倾听他们的声音。这是他们的治疗模式和社区建设模式的承重部分,GK Chesterton 想在你拆掉它之前和你谈谈。
(Alcoholics Anonymous 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比精神病学机构想要的更保守和无情。听力比机构更自由和接受,但关键是没有着陆在完全相同的地方。)
5:
想象一下,你登上了喜马拉雅山峰的顶端,服用了一些不起眼的厄瓜多尔迷幻药,陷入沉思,获得了人生中最深刻的体验。你看到上帝以纯净光之箭的形式接近,它裂开你的头,然后像花朵一样绽放,这让你意识到你的整个童年都是[等等]。
你试图向某人解释这一点,甚至在你说出三个字之前,他们就告诉你你疯了,上帝不存在,你需要每天服用 2 毫克利培酮,直到他们告诉你停止。
这可能是正确的反应,如果有人愿意对最初的嬉皮士这样做,我们可能会为自己节省数十年的怪异艺术和愚蠢的政治。但从里面看,感觉有点刺耳。我偶尔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虽然“最诚恳地警告学生不要将客观现实或哲学有效性归咎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但你有点希望有人至少让你完成你的旅行报告,然后再告诉你“再糟糕和无效,需要一个不糟糕的神经递质平衡。
我不知道从这样的经历中挑选是否有什么收获,但是想要这样做是很自然和人性的。一代又一代的弗洛伊德主义者通过奉承病人的先入之见,即他们的梦想必须有意义,从而过上了美好的生活。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尽量不与患者讨论他们幻觉的含义,因为我的话带有某种科学权威,而《科学》杂志对此没有意见。但有人应该这样做,“让轻度精神病患者为彼此做这件事”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6:
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听力运动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临床主张:尝试与您的声音进行推理甚至与您的声音交朋友比试图压制它们效果更好。
这是真的吗?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精神病患者都说不,至少在第一次检查时不会是微不足道的。大多数声音无法推理。他们没有议程,他们不顶嘴或讨价还价。
但是心理倾向于按照人们期望的方式表现。如果你认为社交团体中的所有朋友和权威人士都说声音会顶嘴和谈判,那么声音会顶嘴和谈判吗?整个西方神秘学传统都说是的。我在这里只是在开玩笑;封闭主义的历史表明,如果你给边缘精神病患者一个非常强烈的假设,即他们使用的技术会产生幻觉并产生某些结果,他们就会得到他们所同意的。
或者内部家庭系统呢?这是一种 woo-y 类型的治疗,治疗师会说“想象你的愤怒正在对你说话,它在说什么?”然后病人试图进行这种想象中的对话。有时他们的愤怒会说一些有见地的东西,比如“我只是想保护你免受再次伤害”,然后病人和他们的愤怒和解,病人变得不那么愤怒了。我自己永远无法掌握这个窍门,但有些人发誓。精神病在这里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与其说“想象你的愤怒会说话”,不如从“你知道你一直听到的那个声音告诉你要杀死所有人吗?让我们先假设这是你的愤怒”。我希望 IFS 为之工作的一些人也会发现它也有效。
所以我是在说“声音不是很聪明和能动,但如果你把某人置于一个奇怪的文化环境中,他们的声音就会开始这样表现”?有点。但更好的框架可能是“在 21 世纪科学精神病学的怪异文化环境中,没有人期望声音是聪明和能动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其他一些奇怪的文化情况下,谁知道呢?”
所有这一切都是口无遮拦的后现代主义者,否认基本真理的存在吗?有点,但是“你对你心灵的主观体验在文化上是相对的”比“现实在文化上是相对的”是一个更弱、更站得住脚的主张,并且得到了很多支持——例如,请参阅Julian Jaynes和Ethan Watters了解更多信息。
7:
Freddie 对 Hearing Voices 以及许多心理健康倡导团体的最大抱怨之一是,他们在“Special Snowflake”这件事上做得太过分了。他们认为患有精神疾病会使他们变得古怪并替代个性。
在弗雷迪的辩护中,他们肯定是这样做的。
你可以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比如:是的,但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对吧?很多患有精神疾病的人都不是很实用。我的意思不是“需要在一个机构工作”功能失调,我的意思是“勉强坚持他们的死胡同并努力支付房租”功能失调。人们需要个人神话。 “我是一个从事 McJob 工作但不擅长的人,这就是我的全部”不会在心理上削减它。 “我是一个白天在做McJob的人,但我的幻觉让我比所有这些表面上比我更成功的人更能洞察世界的问题”只要它不不要被带到一个宏伟的极端。
非居高临下的版本是每个人都处于这种情况。 The Hearing Voices 的人拍拍自己的后背,因为他们有有趣的幻觉,而且比其他人更有创造力。弗雷迪拍了拍自己的后背,因为他坚定不移地承诺认真对待他的精神问题,疣和所有问题,而不是掩饰消极方面。我拍拍自己的后背,因为我平衡且合理地同情双方。真的很难不以某种方式做特殊的雪花事;谨慎在于以不踩到别人的脚趾、与现实大相径庭或使社会变得更糟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8:
由于我们讨论的是特殊雪花这个话题,这一点只与心理健康有关。
现在,我们的社会要求你成为特别的雪花。不够古怪的女人是“基本婊子”,不够古怪的男人是“又一个直白的家伙”。就在今天,我读到一些约会建议,说单身男人需要培养不寻常的爱好或兴趣,因为(它严肃地问)为什么女人想和不“出众”的人约会?
推特上有人抱怨说无聊的人上医学院是因为如果你是一名医生,你就不需要有个性。爱德华·蒂奇抱怨说,人们会以性恋来代替人格。我什至听到有人抱怨说,无聊的人把攀岩当作人格替代品:(他们说)这是最低限度的可行的古怪消遣。没有人愿意被抓住承认他们唯一的爱好是阅读和电子游戏,也许攀岩足以避免被归为大量无聊的人。抱怨者争辩说,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人那么容易逃脱。他们需要更古怪!
一位朋友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说有人移居中国数年,学习烹制稀有品种的豆腐。她嫉妒得发狂;她不是特别喜欢中国和豆腐,但她觉得如果她做了那样的事情,她可以积累足够的古怪点,她再也不用培养另一个爱好了。
在这种环境下,精神病人当然会利用自己的病来换取怪癖!我们对每个人都提出了如此不合理的古怪要求,以至于您必须利用您可以获得的任何优势!
我自己对此感到内疚。我认为我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有趣的人。但这些方式往往是诸如“我写了一个被纽约时报谴责的博客”和“我在一个许多人认为是邪教的群体中”之类的东西——这不是求职面试的正确类型。所以当我遇到不可避免的“告诉我你自己以及你与我们所有其他申请人的不同之处”的问题时,我谈到了我是如何与强迫症作斗争的。这是真的。这不是一场很有趣的斗争,也没有特别塑造我后来的性格。但我永远不会向招生官承认这一点。
在一个层面上,在最后一个招生官被最后一个《纽约时报》记者的内脏勒死之前,人类肯定不会自由。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自己。我们要求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浪漫伴侣、甚至我们的家人表现得古怪。我无法告诉你我妈妈有多少次试图说服我,我整天坐在屋里看书很糟糕,如果我开始攀岩或其他什么,我可能会更“全面”。我们可以随时停下来。我们可以承认,除了负责任和富有同情心之外,您不需要“个性”。如果你擅长工作并支持你的朋友,你也不需要搬到中国去研究稀有品种的豆腐。
但是,如果您确实坚持将不寻常的经历作为衡量一个有效人的标准,那么总会有夸大您的经历有多不寻常的压力。每个人要么攀岩,要么养成人格障碍,这是两种选择。还有很多人恐高。
9:
我认为精神病患者探索他们的精神病,在他们自己之间,以服务于他们的心理需求的方式,和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关于它的文章,你应该得出结论他们是对的、好的和愚蠢的,这是有区别的希望他们服药的广场精神病院只是愚蠢和脱节。
我一直在关注想要庆祝跨性别者并反对他们的耻辱的亲跨性别活动家与想要阻止一群孩子听到跨性别很酷且如此过渡的反跨性别活动家之间的冲突。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我会尽力谈论它,我很抱歉可能冒犯了双方。
我对此进行任何讨论的出发点是,我觉得对于一个消息灵通和善意的人来说真的很难不同意,至少有很大一部分跨性别者没有有意识地伪造它。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有感觉自己是异性的体验,如果被迫以他们的出生性别生活,他们绝对会非常痛苦,并且告诉他们“不,只是摆脱它”是行不通的,一点也不。我认为很难在不得出这个结论的情况下密切了解变性人,除非你有某种超出我想象的真正银河系头脑。
那么对于那些相信跨性别是一种“社会传染病”或“特殊雪花”的人来说,还有什么?如果我不得不强化他们的立场,那将是这样的:有一些开关可以被社会压力翻转并且想要看起来很酷。一旦开关被翻转,你就会以某种非常真实的方式变性:你不是在假装它,在你被允许变性之前你会很痛苦。尽管如此,变性人会让人们在网络上变得更糟,所以社会应该尽量避免翻转这个开关。
(如果您经常阅读此博客,您可能会注意到与我的厌食症理论的相似之处:是的,很多人开始节食是因为他们想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之类的,但极端节食似乎会触发一个开关,这个开关会变成生物,而且你不能仅仅通过说服厌食症患者不再想成为芭蕾舞演员就让他们恢复健康饮食)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项最大程度地富有同情心的政策将包括试图支持已经跨性别的人,并试图防止在尚未跨性别的人身上发生转变。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明确提倡这项政策,可能是因为它真的很难做到正确——你越努力避免在易受影响的年轻人面前谈论它,你就越有可能对现有的跨性别者进行污名化,反之亦然。在这个问题上有足够多的恶意,我敢肯定任何一方都不会相信对方会尊重这样的妥协。也许他们不信任他们是对的。尽管如此,当我试图弄清楚我个人应该如何表现时,我会考虑这些因素。
这也是我对听到声音的感受。听到声音是否具有社会传染性?我的猜测是轻微的。 DSM 表示,如果某人在文化背景下被期望并鼓励他们听到声音,则您无法诊断出精神病性障碍——这听起来确实像专家认为文化背景会影响您是否听到声音。重生的基督徒经常有通常被归类为精神病的经历——我问过一群福音派人士,他们说“上帝告诉我 X”,他们是否真的以一种,你知道的,听到上帝的方式听到了上帝,他们通常说是的。再次, 阅读您的 Jaynes 。谨慎的做法是不要告诉所有人听到声音是完全正常和酷的。
我不觉得听力运动正在这样做,确切地说。他们只是坐在那里,成为已经有这种经历和问题的人的接受场所。我确实认为《纽约时报》关于他们多么酷、多么容易接受和多么正常的文章——以及他们比仅仅服用药物的无聊人要好多少——可能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
10:
这篇文章谈到了同伴心理健康顾问 – 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试图帮助其他患有相同疾病的人。
一些同行心理健康顾问是我认识的最好和最富有同情心的人之一。这是一项艰巨且低薪的工作,由可能自己苦苦挣扎的人完成,但他们做得非常出色,并且可能在我几乎无法想象不得不在其中进行手术的情况下挽救了很多生命。
其他同行心理健康顾问很糟糕。一个读了很多关于某种疾病的教科书和期刊文章的医生的傲慢不能与一个自己克服了这种疾病并认为这意味着他们知道每个人都必须做的真正标准化的方式的同行的傲慢相提并论这。
此外,“克服这种情况”对于这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延伸目标。我还记得一个病人问我能否在一周内治愈他的焦虑。我告诉他绝对不会——药物甚至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控制焦虑可能是一个终生的过程——为什么他还需要在一周内治愈呢?他说他是一个关于“我是如何克服焦虑的”主题的鼓舞人心的演讲者,他计划下周发表演讲,但太着急了,无法继续工作。我经常想起这个人。
最糟糕的失败模式是那些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处理(或“处理”)他们的病情的人,相信其他人也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并迫使其他患者远离药物——让他们觉得他们正在屈服于邪恶的精神病院,如果他们甚至考虑吃药的话。纽约时报的文章读起来就像是其中一个人写的。
11:
关于这篇文章本身,我没有太多要说的,除了恳求你在打开报纸时随身携带我的《阅读关于精神病学的流行媒体文章的备忘单》,但我确实认为值得谈论世卫组织的角度。
这篇文章的很多反医生反医学宣传都依赖于世卫组织的一份报告, 《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指南:促进以人为本和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 。它写道:
去年 6 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长达 300 页的关于精神健康客户人权的指令——尽管它产生于庞大的官僚机构,但它是关于严重精神疾病主题的革命性宣言。它挑战了生物精神病学的权威、专业知识和对心理的洞察力。它呼吁结束所有非自愿或强制治疗,并结束在精神卫生保健中最重要的药物方法的主导地位,包括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和许多其他诊断。世界卫生组织坚持认为,精神病学的问题药物必须不再是毫无疑问的支柱。
该指南是 WHO 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许多说药物糟透了,精神病学不好的患者权利倡导者聚集在一起,他们一起写了一份报告,说药物糟透了,精神病学不好,然后 WHO 在清单上划掉了他们恭敬地听取了那些认为毒品很烂而且精神病学不好的人的意见。
例如,如果你看一下这份报告,第一个被认为是“关键国际专家”且其观点所依赖的人是西莉亚·布朗,她的传记将她描述为:
西莉亚·布朗 (Celia Brown) 是一名精神病 [虐待] 幸存者,也是心理健康人权运动的领导者。西莉亚在国际心灵自由委员会任职数年,包括担任 MFI 主席……这里展示的是西莉亚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年会前的 MFI 抗议活动中发表讲话
我很高兴有这样的人存在;他们让我们其他人诚实。但是如果你把一百个这样的人聚在一起,他们会说像这样的人说的话。如果你把它做成一个有光泽的报告,并在上面贴上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志,那么就会有一个有光泽的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上面写着人们喜欢这样说的话。没关系,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被允许制作 PDF,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纽约时报》似乎试图用它来暗示临床医生或专家或你应该关心其意见的人承认药物不会工作和待遇都不好,这个建议是错误的。
请,请只使用备忘单。
12:
通常的人性和人道的规定——食物、住所、咨询、接纳、支持、友谊——会产生很大的不同。不仅仅是抑郁症。即使在你所期望的精神病之类的事情中,它们也太生物学了,无法通过像这样的模糊事物来影响。有很多人在压力下患有精神病,但在理想的环境中表现良好。无论您做什么,都有很多其他人会患精神病,但是根据环境的不同,他们的精神病可以是良性的并且与幸福的生活相适应,而不是暴力和无法控制的。
但是这些东西并没有无限好,有时你需要药物。
(药物也不能无限好,但药物和社会心理支持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通常有一些药物可以让病人停止做危险和破坏性的事情,但这个剂量可能不会让他们很开心或能够做任何事情。这形成了一个困难且道德上有问题的权衡——你如何平衡病人自己的舒适度和他周围不希望他破坏的人的舒适度?社会心理支持的部分作用是为患者提供一个人们愿意容忍偶尔出现的怪异或破坏性事物的环境,从而使这种权衡的折衷点对患者的需求更加富有同情心。)
人们喜欢把精神科医生描绘成思想封闭的偏执狂,他们认为药物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可能方法。这对某些人来说是正确的,但却是对其他人的侮辱;与 Johann Hari 的想法相反,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并不是一个严格保密的秘密。
但与此相反的是那些认为社会心理干预和接受是解决任何事情的唯一可能解决方案的人,他们一有机会就乱说药物。
我的指导之星一直是耐心的选择——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下,法律系统正式将其取消以保护他人。这意味着患者有机会做除服药以外的事情。这也意味着不要试图吓唬病人远离药物或用 NYT 质量的胡言乱语误导人们。
我认为在心理健康的帐篷中,听力运动和类似的事情有空间——只要他们不试图把其他人踢出帐篷,并说他们的方式是一刀切的解决方案每个人。
原文: https://astralcodexten.substack.com/p/in-partial-grudging-defense-of-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