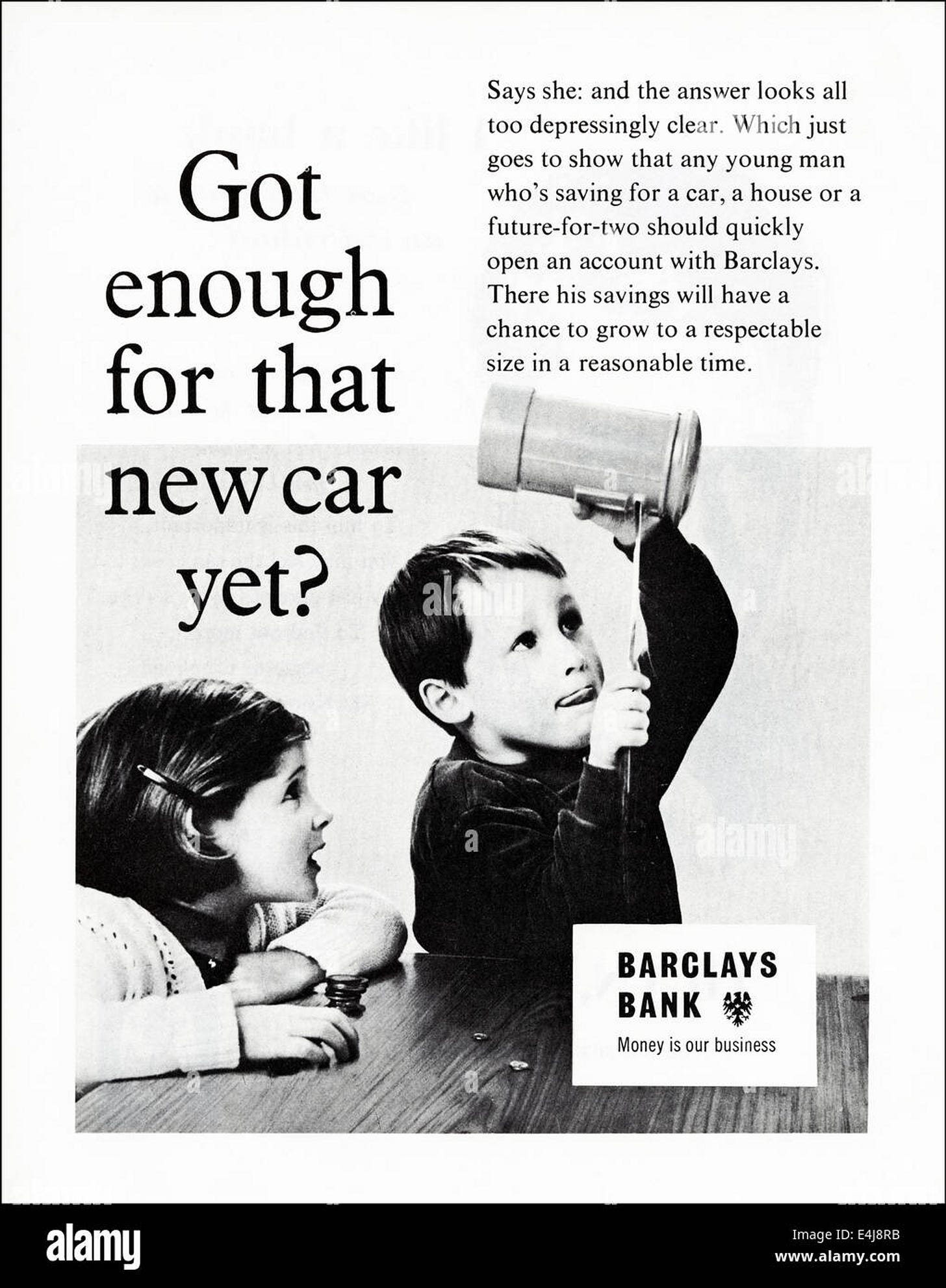我
我最喜欢的政治节目曾经是 Veep,该节目讲述了由 Julia Louis-Dreyfus 扮演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虚荣和残忍的副总统 Selina Meyer。它使用了政治候选人为赢得胜利而采取的极端做法的例子。她撒谎、欺骗、混淆视听,对她无能的员工极其残忍,而这些员工本身就是人类的漫画。最重要的是,她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自恋的反社会人士在办公室时会是什么样子,她的核心技能是想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侮辱。
好吧,她曾经是。
关于她不明智地使用 Twitter 和制造假新闻有多个情节点,这在节目中被证明是性格缺陷和她无能的一个例子。然而,现实是,不需要引用!对于竞选财务,或几乎无法将句子串在一起的候选人,或纯粹的裙带关系,或极其无能的腐败,情况也是如此。除了精彩的对话,我们几乎超越了这部剧的所有内容。
赛琳娜甚至比希拉里早几年就有了自己的电子邮件丑闻。还记得 Jonah Ryan 在反对 vax 获得选票后感染了水痘吗?
讽刺对于我们这个物种来说曾经是一口深井。我们使用夸大版本的事件和人物来更好地理解它们。批判和学习。从纽约客卡通到关于种族的笑话,我们通过夸张和笑声来学习。
在一个被杂音包围的世界里,唯一能引起注意的方法就是偶尔夸大其词。
现代世界已经扼杀了这一点。
Veep 并不孤单。硅谷曾经是我最喜欢的科技节目。对于贪婪的亿万富翁、社交无能的程序员和风险投资家来说,这已经足够真实了,但如果你今天看的话,几乎所有的笑话都不会发生。而且不仅仅是 brogrammers。它对虚拟现实的描述几乎重新流行起来,它看起来就像元宇宙,更不用说除了 Gilfoyle 之外的人也认为是有感觉的友好聊天机器人。该公司通过数据压缩、区块链和最终的 AI 进行转型似乎预示着 2022 年的结束。现实生活已经完全摧毁了笑话的极端、反应的空洞、人们的健忘和周围世界的疯狂。
但后来我们有了 FTX及其相关的恶作剧,任何有自尊心的作家都不会将其包含在他们的节目中,因为它们太“离谱”了。我们让马斯克和 Twitter 接管了它,伴随着相关的崩溃、清洗和反向清洗,这个节目看起来很平淡。
斯蒂芬·科尔伯特 (Stephen Colbert) 有长达十年的讽刺作家生涯,我认为这在今天行不通,因为他太接近真实的东西了。洋葱经常被误认为是真正的新闻工作。不仅是国际足联副主席引用了一篇洋葱文章称美国将举办 2015 年世界杯(真的!),还有 2011 年一篇关于美国国会大厦被围困的文章到 2022 年就被淘汰了。
Onion 在 2011 年表示:“总统宣布计划通过印钞并将其从直升机上扔出去来创造就业机会”,而“直升机撒钱:特朗普总统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可能会在 2020 年达成紧急经济计划”。
我们设想的笑话已经成为事实。讽刺已经死了。我们杀了它。
二
凶器是什么?好吧,对夸张的热爱从一把手术刀变成了一根大棒。如今诞生的大多数公司都以“改变世界”为目标。广告活动通过极度快乐、女性或男性的巨大成功以及如果您不购买所销售的任何东西将如何被排斥来展示用户利益。事实上,当有一个实验来测试这一点时。
这些实验表明,极度夸张更清楚地传达了说话者的预期交际目标是什么,但并没有提高说话者实现该交际目标的有效性。
许多对广告夸张的关注始于 19 世纪的英国。特别是与医疗骗术领域。正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人们总是对购买改善健康的东西很感兴趣。正如人们可能想象的那样,一旦人们开始发现可以改善健康的东西,人们也开始销售各种假货(包括假蛇油),声称它们与真货一样强大。从那时起,关于广告的争论就开始了。
庸医辩论的情况导致了对广告作为认识论上值得怀疑但并非非法领域的观点的法律阐述和形式化。其次,广告作为夸张的地位是受法律支持的文化分工或法律边界工作的一部分,它在现代英国为科学和市场划分了不同的角色,科学越来越受到限制,而市场越来越受到限制。
从那以后,事情只会变得更加极端,尽管根据至少在过去十年中进行的一项研究,这显然现在正在略有下降,这似乎令人鼓舞。
但新闻也是如此。自 24 小时有线电视新闻和大多数新闻媒体的小报化以来,几乎每个人都至少以轶事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这意味着它们通常不是诱饵。手工制作,让你想要点击夸张的声明,最令人震惊的是头条新闻。
Media Insight Project 2019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68% 的美国人认为新闻媒体夸大了他们对某些问题的报道。这比 2016 年有这种感觉的 55% 有所增加。
此外,皮尤研究中心 2018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45% 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新闻机构在报道有争议的话题时,经常会弄错事实。这个数字比 2016 年有这种感觉的 34% 有所上升。
三
当我们慢慢适应失去这个工具时,我们失去的是我们正在失去用共同语言看世界的能力。我们的夸张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界限,没有它们,我们就像没有护栏一样。
不久前,讽刺是批评权势者的有效工具。从伏尔泰到马克吐温,作家们用讽刺来指出当权者的虚伪和愚蠢。
罗森等人将讽刺视为让公民参与政治的有效手段。即使像约翰奥利弗这样的事情让他的观众更容易理解公司的游说做法,幽默和夸张的使用对于让想法进入奥弗顿窗口和解决方案领域具有独特的帮助。
讽刺也有更强大的捍卫者。凯特·沃森 (Cate Watson) 的一篇论文谈到讽刺如何成为批判性分析的一种形式。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David Foster Wallace) 著名地指出,我们生活在“反讽终结”的时代,下一步将成为后反讽,回归真诚。这似乎没有实现。他还在 E Unibus Pluram 中提到讽刺是一种强调社会缺陷的工具,尽管是直截了当的。
讽刺传统上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武器。我之所以提到所有这些,是因为在我看来,许多最好的当代小说都是讽刺小说,而阅读这些小说的一个原因就是嘲笑我们社会中所谓的“正常”事物的荒谬之处
或者正如冯内古特所解释的那样。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么还有什么新鲜事呢?今晚先是好消息,然后是坏消息。坏消息是火星人已经降落在纽约市,他们已经入住了华尔道夫酒店。好消息是,他们只吃各种肤色的无家可归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而且他们会撒汽油。
在后现代背景下尝试讽刺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被嘲笑的规范早已不再普遍。现在几乎不可能了。例如,您知道奇爱博士是一部纪录片吗?
即使我们已经摆脱了公开的愤世嫉俗,如果这是真的,我们也拥抱了彼此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系,这使得以前的过度行为看起来很正常。对于现在丢失或损坏的这个工具,就相当于我们失去了正确看待周围世界事物的能力。它消除了我们同情的能力,并且减少了我们对极端应该教给我们什么关于中间的理解。
从历史上看,讽刺有 3 种类型。 Horatian satire,比如 The Onion,它专注于指出我们有多糟糕的笑话。有 Juvenalian 讽刺,如 A Clockwork Orange,揭露一个想法并激怒我们。还有梅尼普式的讽刺,平衡了两者。
上面的例子大部分都是第一种,Horatian。如果我们阅读洋葱并且它没有以前的咬合力,那么它的重点就丢失了!如果它消失了,另外两个也会消失。如果没有它来记录我们在任何时候离深渊有多远,任何推动积极议程的尝试只会显得荒谬。就像今天一样,用最轻的唤醒触摸。
生活在讽刺的尽头是一件令人筋疲力尽的事情。不断提醒你生活在动荡的时代,而极端是正常的,这需要付出巨大的精神代价。要保持适应性或为这种混乱建立任何类型的弹性,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我们不能再伸展自己来测试边界,我们生活在脆弱的笼子里。讽刺的另一边剩下的就是闹剧。
我不认为潮流会很快转向。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如果我们要使用隐喻并引导我们内心的 Silence Dogood 在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和虚伪中寻找幽默,我们将不得不等待文化赶上来。否则,我们注定终生只能接受止痛药笑话和滑稽的笑话,现实胜过任何与娱乐相去甚远的事物。
我们以前没来过这里,没有简单的课程。但一如既往,当我们跨过门槛进入新时代时,想象一下我们周围看到的戏剧就是这样,戏剧,我们开始扮演自己是很有用的。
感谢阅读 Strange Loop Canon!免费订阅以接收新帖子并支持我的工作。
结尾
为了完整起见,以下全视人工智能的其他几个答案说明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可能的答案 1。
24 小时新闻周期、社交媒体和我们自己的确认偏见创造了一个我们只消费支持我们现有世界观的信息的世界。在政治方面尤其如此。我们不再能够将对方视为具有正当观点的人类,而是必须消灭的敌人。
这对讽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使讽刺发挥作用,需要对被讽刺的内容有共同的理解。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中,往往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没有聚在一起嘲笑我们周围世界的荒谬,而是退回到各自的回音室,在那里我们只与同意我们的人交谈。
可能的答案2。现实生活使虚构的夸张看起来更加残酷,因此没有抓住重点。
如果我现在看《宋飞正传》,我会为幽默的冷酷无情、角色对其他人的同情心如此之少而畏缩。自我吸收! George Costanza 试图通过假死来摆脱一段关系;杰里约会一个女人只是因为她有大乳房;伊莱恩和一个男人分手,因为他吃了她的糖果;克莱默是个到处都是讨厌鬼的将军。他们都是可怕的人,但我们爱他们,因为他们很有趣。
但是,我们想嘲笑人们彼此可怕吗?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角色成功吗?当现实生活已经充满自私和残酷时,我们还需要在屏幕上看到更多吗?
不仅仅是讽刺已经过时或者它的目标已经转移。正是讽刺的想法——用夸张和嘲讽来揭露愚蠢和罪恶——在现代世界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我们再也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模仿的;一切都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模仿。我们的现实已经荒诞到无以讽刺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