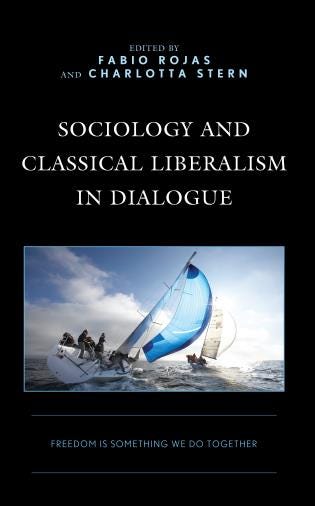1990 年 1 月,我认识了法比奥·罗哈斯 (Fabio Rojas),当时我们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生。 1994年,他是我婚礼上的伴郎。现在他是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去年,他和夏洛塔·斯特恩出版了《社会学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对话:自由是我们一起做的事情》。经他许可,这里是这本书的简介。 多年来,人道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是一个自由主义非营利组织,举办研讨会,其目的是让学生和教师建立联系并讨论自由社会的想法。 1993 年夏天,我参加了其中一场研讨会,花了几天时间讨论奥地利经济学、自发秩序理论和个人权利理论。我有机会见到自由意志主义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历史学家拉尔夫·莱科、法律学者伦纳德·利吉奥和活动哲学家汤姆·帕尔默。 有一次讲座让我觉得很奇怪,三十多年后我仍然记得它。这是一场关于社会学的讲座,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现代社会学与进步的政治价值观密切相关。我想知道谁被邀请来做这次演讲,因为到目前为止我遇到的每一位社会学学生和老师都极度左倾。令我惊讶的是,IHS 聘请了一位名字已被遗忘的商人来向政治精英发表社会学演讲。我心想:“社会学和自由主义是如此对立,以至于他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社会学家来建立联系。他们必须随机找一个人来做这件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一个明显的规律:社会学和自由主义从未交叉。在自由主义学术活动中,我几乎从未遇到过研究社会学或自称社会学家的人。同样,当我开始作为学术社会学家的职业生涯时,我从未遇到过另一个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或古典自由主义者的人。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对我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一个致力于社会学研究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人被视为活生生的矛盾。我曾经在“学生争取自由”活动中发表演讲,一位社会学学生走过来告诉我,他对我的存在感到震惊。 我从个人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社会学和古典自由主义的界限是要避免的。也许这两个传统的观念太不一致了。即使我能够化解紧张局势,可能关心的人也几乎为零。研究这个话题简直是白费力气。 当我开始遇到其他对社会学和自由主义如何相互对话感兴趣的人时,事情发生了变化。我曾经见过安妮·沃瑟姆(Anne Wortham),她获得了博士学位。获得波士顿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并写了一本名为《种族主义的另一面:黑人种族意识的哲学研究》的书。她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后来定居于北伊利诺伊大学。我遇到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夏洛塔·斯特恩(Charlotta Stern),她在《独立评论》等期刊上发表了关于社会学领域自由主义思想匮乏的文章。我还遇到了源源不断的学生,他们植根于社会学,但希望更多地了解古典自由主义思想。 最终,我决定事情需要改变。有人需要创造一个知识空间,让社会学家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可以互相交谈。我联系了夏洛塔·斯特恩,询问她是否愿意帮助我编写一本探讨这一主题的著作。这就是《社会学与古典自由主义对话:自由是我们一起做的事情》的诞生。 它可以在 Rowman & Littlefield 网站上免费下载。 这本书既是一次智力探索,也是一次社区建设的练习。我们询问这两种传统如何通过提供新的研究问题来丰富彼此,但我们也要求社会学家和古典自由主义者进行真正的对话。 我们邀请了刑事司法、人口学和政治学等相关领域的社会学家和学者,询问古典自由主义和社会学的相互作用如何照亮他们的研究领域。例如,约翰·冰岛和埃里克·西尔弗邀请社会学家考虑市场自由化与全球减贫相关的大量证据。布兰登·戴维斯依靠公共选择理论来描述国家如何通过大规模监禁来掠夺少数族裔人口。劳伦·霍尔(Lauren Hall)运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认为,解决健康差异的最佳方法是市场竞争,而不是国家监管。 受到本书各个章节的启发,夏洛塔和我向社会学传达了一些重要信息。首先,我们认为社会学需要考虑其以自由为导向的思维的本土传统。虽然社会学家经常崇拜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和韦布·杜波依斯等社会主义人物,但过去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例如赫伯特·斯宾塞、亨利埃特·马蒂诺和耶鲁大学教授、美国社会学协会前主席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社会学家不需要假设社会学固有的集体主义,而是需要理解其核心存在着充满活力的个人主义传统,并且需要复兴。 其次,古典自由主义者可以提出能够产生重要社会学见解的研究问题。例如,古典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自由市场是解决贫困的最佳方案。因此,社会学家可以研究市场自由化如何直接让穷人摆脱严峻的物质条件,这一立场与当前许多关注资本主义贫困不可避免性的贫困研究相矛盾。 第三,古典自由社会学可以成为社会学专业的“第三条道路”。大多数社会学家要么是技术官僚,他们相信冷静的社会科学可以为国家政策和政府监管提供信息,要么他们持有与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种族理论一致的强烈反资本主义观点。相反,社会学的实践方式可以反映出对言论自由、开放市场和有限政府等体现自由的制度的深刻欣赏。 有些人认为社会学由于其强烈的左倾倾向而毫无希望。夏洛塔和我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我们相信社会学可以而且应该包括不同的规范观点。我们邀请您阅读这本书并参与这次对话。
© 2025布莱恩·卡普兰 |
自由社会学
法比奥·罗哈斯 (Fabio Rojas) 的客座文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