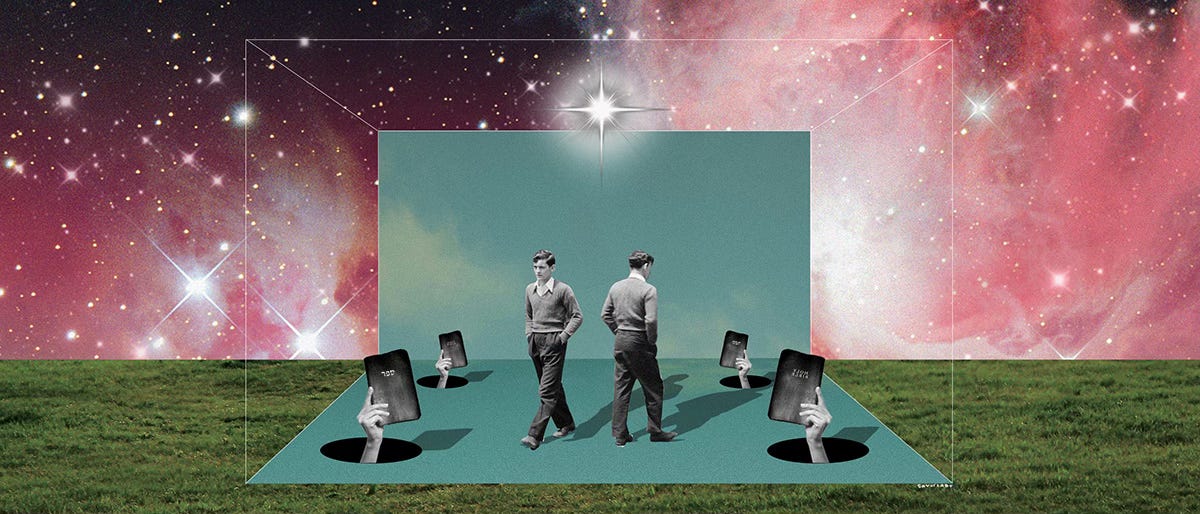在 2000 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有时似乎整个互联网的创建只是为了两个目的:访问色情内容和辩论上帝的存在。
这是所谓“新无神论”的鼎盛时期——想想理查德·道金斯和萨姆·哈里斯——当时,宗教激烈的争论如此普遍,以至于与宗教完全无关的论坛通常会专门设立一个专门的部分来进行此类讨论,只是为了防止它们压倒网站的其他部分。 (写下这句话让我感觉自己老了。)
我从来没有对自己观看的色情作品表现出尖锐的态度,但我对自己的无神论态度却很尖锐。并不是说一本山姆·哈里斯的书,甚至是一篇拼写错误的互联网帖子,才让我走到了那一边。我在一个世俗家庭长大,没有太多关于神的谈论,除非你算上我童年对牙仙子的热爱,否则我不记得曾经有过如此多的信仰。就连我们偶尔敷衍出现的寺庙里的拉比也说我们不必相信上帝,尽管我一直怀疑他只是想通过假装比实际更悠闲来引诱我们,就像人们在第一次约会时所做的那样。
那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感觉很重要,不仅仅是因为你相信的一切在你十五岁的时候都感觉很重要。这是乔治·W·布什时代的顶峰,看起来宗教狂热分子确实控制了这个国家,如果我们能够说服足够多的人减少宗教信仰,我们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会立即得到解决。 (当然,就像我青少年时所想的一切一样,结果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谁知道后宗教右派会更糟?)
我从来没有去寻找上帝,但我确实在寻找一些东西。就像许多想要让自己相信自己的不当行为是有意义的年轻人一样,我变得有点寻求者。我确信那里还有更多东西,而且我迫切地想要找到它,即使我无法准确解释它是什么。我想当我看到它时我就会知道它,但要么我看到了它但我不知道它,要么我一开始就从未见过它。
我尝试过冥想、迷幻药和全力以赴的野心;我尝试过音乐会、性实验和长途散步。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尝试宗教,如果有人建议这样做,我会嘲笑他们,就像莎拉嘲笑上帝时,他说她会在九十岁生孩子一样——我当时不会得到这样的参考。
在我生命的这个阶段,我可能没有找到我所寻找的东西,但一路走来,我经历了许多我称之为神秘甚至精神的经历。我盯着草地上的手臂,直到它们之间的界限消失,我看到的只是原子旁边的原子。第二天,我沉浸在对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的笑声中——当时甚至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不知何故,毫无意义才是重点。
但所有这些经历似乎都与毫不妥协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相容,而且没有一个给我带来神圣感。我认为我将永远是一个无神论者。
我失去了我的无神论,就像海明威所说的破产一样:逐渐地,然后突然地。
渐进部分:我开始从纯粹智力的角度对宗教产生兴趣。在我年轻时的沾沾自喜中,我拒绝了一些我知之甚少的东西,当然,不相信某件事并不是完全避免了解它的好理由。我也不相信纳粹主义,但我仍然读了很多关于第三帝国的书,以至于我的书架上有专门的部分。
此外,我长期以来一直为自己拥有广泛的知识基础而感到自豪。我知道理查德·尼克松辞职那天吃的具体饭菜,但不知道《申命记》中发生了什么,这真的有意义吗?几乎每一种人类文化都曾发展出某种形式的宗教。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是真的,但它确实意味着可能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东西。
所以我从头到尾读了整本圣经;结果很无聊,但我仍然很高兴我做到了。我发现自己正在寻找更多宗教思想家的作品,或者至少当我偶然发现它们时,除了立即驳回之外,我还做出了一些反应。我并没有成为一名皈依者,但我对拥有深刻、真正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样子感到非常好奇。如果我们开发出某种高保真科幻大脑模拟器,那将是我厌倦了所有性爱内容后下载的第一个程序。
突然的部分:我在旧金山郊外的一个老嬉皮士农场里,与十几个陌生人和一个秘鲁萨满一起喝了一个空的佳得乐瓶子里的死藤水。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在寻找上帝——我这样做根本没有任何原因,真的,除了无聊的好奇心。机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就像湾区经常出现的那样,我答应了,因为这似乎比拒绝更有趣。
读到的最烦人的两件事是精神启示和迷幻体验,所以我不会冒着激怒订阅者的风险,对一个结合了两者的夜晚进行太多细节。可以这么说,在我吐完泥土后的短暂瞬间,我确信我触摸到了一个我只能形容为上帝的东西的脸。
也许这种经历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即使是最坚持的唯物主义者也会动摇。或者也许这只是我的不相信的叠叠乐塔中拉出的最后一个方块。不管怎样,当我周日早上开车回家时,令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我意识到我不再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
那次经历让我不再称自己为无神论者。但这并没有让我开始给自己起别的名字。
要让我成为一名彻底的宗教信徒,需要在农场度过一晚以上的时间。我也不能让自己认定自己是不可知论者,这个词总是让我充满不可否认的非理性仇恨。这是一个狡猾的词,表明某人没有充分考虑这个问题,或者太过懦弱而不愿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不确定他们相信什么;我确信我所相信的,只是我所相信的是我不确定的。我知道这两句话听起来像是同一件事,但我发誓我的想法有所不同。
在很多方面,无神论者仍然感觉最接近我实际到达的地方,至少现在是这样,那就是可能不存在任何传统意义上的上帝,而且如果那里有更大、更神秘的东西,那么它几乎肯定与人们通常所说的“上帝”有很大不同,以至于使用同一个词感觉就像将语言延伸到了突破点。但称自己为无神论者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确定性不再正确。
也许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就像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是一名石匠:他抽了锅,但没有吸入。我看到了上帝,但我不相信。或者也许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就像我是异性恋一样:有一个模糊的夜晚,我只是不计算在内。
我认为,对《上帝错觉》这样的书所引起的轩然大波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这是无神论的胜利。文化在不断发展,没有什么能长久地引起争议:艾斯·库珀从杀死警察到和埃尔莫一起出去玩,在《继承之战》的十分钟内,你会听到乔治·卡林在电视上不能说的全部七句脏话。
与其说无神论者获胜,不如说整个问题不再那么重要了。或者至少,它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在农场的那个周末之后,我的朋友们都问我是否受到了任何惊天动地的启示的打击,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回应。一方面,你可以说有没有神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犹豫不决对我的生活的实际影响为零。你所相信的比你实际所做的要重要得多,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许多宗教传统即使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也强调实践。
如果有一个神能体验到任何接近人类情感的东西,我不禁想象它不会真正关心我们是否相信它,并且可能会对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花费的所有时间和精力感到非常好笑。据我们所知,上帝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地质构造,而我们只是那些偶尔弄乱岩石的无足轻重的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