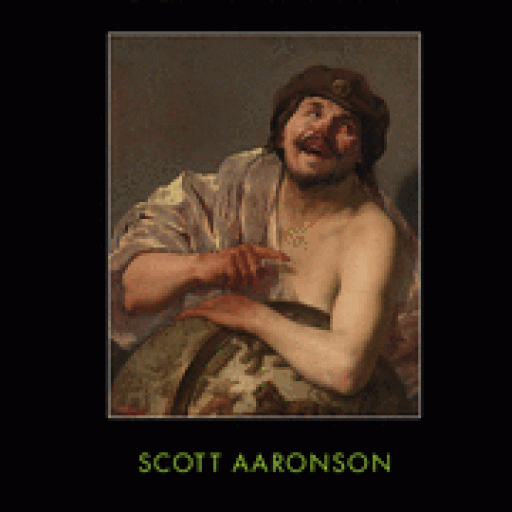
每周,我都告诉自己,我不会再发表有关小行星撞击美国学术界的帖子,但每周发生的事件都迫使我采取其他行动。
世界上没有人——当然没有读过这篇博客的人——可以说我对美国大学的反犹太主义问题感到厌倦。我曾抨击以色列国(以及地球上所有国家中只有以色列)应该被根除的教条主义信念对整个院系、不相关的学生俱乐部和校园公共区域的接管,并利用这种信念作为进入的试金石。自 10 月 7 日以来,我几乎每天都会处理一些评论和电子邮件,称我为种族灭绝的犹太法西斯复国主义者。
因此,我希望当我说:今天我向哈佛大学勇敢地面对特朗普政府致敬时,这能有意义。当我本周晚些时候访问哈佛数学系并进行第五届年度叶氏讲座时,我会亲自这么说,主题是“多少数学是可知的?”我发现,消息越令人沮丧,我的思绪就越会转向困扰欧几里得、阿基米德、莱布尼茨、罗素和图灵的同样问题。事实上,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不分享这次演讲的摘要呢?
多年来,理论计算机科学一直在寻找越来越精确的答案,以解决以下问题:哪些数学真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有限存在来说是可知的,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受物理定律的约束。我将讲述一个故事,从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和图灵发现不可计算性开始。然后我将介绍令人惊叹的 Busy Beaver 函数,它的增长速度比任何可计算函数都快。我和 Yedidia 的工作以及 O’Rear 和 Riebel 最近的改进表明 BB(745) 的值独立于集合论的公理;另一方面,去年的一项国际合作证明了 BB(5) = 47,176,870。我将推测 BB(6) 是否会被我们或我们的人工智能继任者所认识。接下来我将讨论 P≠NP 猜想以及它对于机器智能的限制意味着什么和不意味着什么。由于我自己的专业是量子计算,我将总结我们对可扩展量子计算机的了解,假设我们得到了它们,将扩展数学上可知的边界。最后,我将讨论甚至超越量子计算机的假设模型,如果一个人能够(例如)跳入黑洞,创建一条封闭的类时曲线,或者将自己投射到宇宙的全息边界上,这可能会进一步扩展可知性的边界。
现在回到令人沮丧的消息。让我站在哈佛一边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在政府介入之前,哥伦比亚就已经在打击反犹太主义和执行反破坏规则方面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然后,一旦政府确实取消了资助并提出了最后通牒——完全超出了第六章法律规定的程序——哥伦比亚政府很快就同意了一切要求,引起了左倾教师的愤怒。然而,尽管政府完全投降,但它仍然继续扣押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研究和其他科学经费,同时发明了一份永无休止的额外要求清单,其明显的终点是哥伦比亚大学像俄罗斯或伊朗的大学一样接受国家意识形态控制。
通过采取这种焦土路线,政府已经尽可能清楚地向所有其他大学发出了电报:“实际上,我们不在乎你们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们只是想摧毁你们,而反犹太主义是我们最好的借口,这是你们最明显达不到理想的地方。但我们并不是真的想治愈病人,或者强迫病人养成更好的健康习惯:我们只是想开枪,开膛破肚,肢解病人,既然如此,你还不如和我们战斗,有尊严地死去!”
难怪我杰出的哈佛朋友(以及过去的Shtetl-Optimized客座博主)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和博阿斯·巴拉克(Boaz Barak) (不完全被称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觉醒激进分子)在法庭上支持哈佛对此进行斗争。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拉里·萨默斯 (Larry Summers)也是如此,我们也欢迎他在这里发表客座博客。他们都明白,事件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像没有反犹太主义一样与特朗普作斗争,尽管我们仍在继续与反犹太主义作斗争,就好像没有特朗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