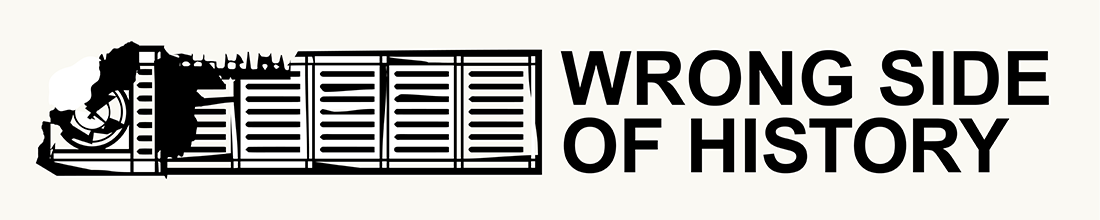上周我和一位英国裔以色列朋友一起参加了“带他们回家”集会。当我们排队通过安检时,一位女士正在分发英国国旗,并以抱歉的方式问我们是否想要,并解释说“你不必”。我们都觉得拒绝是不礼貌的,但我觉得挥舞旗帜实在太尴尬了,所以我只是笨拙地把它放在身边的袋子里,直到旗帜从杆子上掉下来,所以我只能拿着一根小棍子四处走动。 与前一天我出于好奇观看的亲巴勒斯坦活动的狂欢气氛不同,这次的气氛非常阴沉,略带焦灼。尽管展示了以色列国旗,但它也给人一种非常英国的感觉。发言者谈到了他们对英国的热爱、对王室的忠诚,以及,在一个例子中,当人们能够公开表达对哈马斯的支持时,他们有一种不认识自己的家的感觉。 《历史的错误面》是一本由读者支持的出版物。要接收新帖子并支持我的工作,请考虑成为免费或付费订阅者。 我去是因为我对 10 月 7 日发生的事情感到恐惧,并且感到一种不适,因为许多人并不具有同样的厌恶感。如果类似的大屠杀发生在英国,而我看到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庆祝它——或者至少说英国是因为其殖民历史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会被压垮。 但我并不是真的去那里,因为中东,这感觉像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英国对此无能为力,但更多的是因为想到我的一些同胞送孩子上学感到不安全,这让我感到难过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我认为参加集会的外邦人更有可能是保守党,而大多数签署《十月宣言》的人,包括我在内,似乎都是保守党。事实上,就像大调整以来的几乎所有问题一样, 现在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态度与党派路线强烈一致。正如马特·古德温指出的那样,现在只有十分之一的工党选民更加同情以色列。 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事实上,正如威廉·阿特金森最近为 ConHome 所写的那样, 保守党阿拉伯主义的衰落是近年来的显着趋势之一。他引用了克里斯平·布朗特(Crispin Blunt)的例子,“一个习惯于犁出孤独犁沟的人”,现在他是周围为数不多的亲巴勒斯坦保守党议员之一。 虽然布朗特指责政府通过支持以色列来“协助和教唆战争罪行”,但“保守党议员中的亲以色列倾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而阿拉伯主义倾向则更弱。” 今年,瓦尔西女士成立了一个新的亲巴勒斯坦保守党团体,还有极少数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保守党议员,比如史蒂夫·贝克,他们似乎热衷于代表选民的利益。但他们很少见,相比之下,以色列保守党之友 (CFI) 声称大约 80% 的保守党议员是支持者。 正如阿特金森指出的那样,这种亲以色列的倾向不能归结为选举算计:“基于(并非无理)的假设,即犹太选民更同情以色列,而穆斯林选民更同情巴勒斯坦,”阿特金森写道:“基本的计算能力会看到国会议员们对英国近四百万穆斯林的支持超过了对三十万左右犹太人的支持。 根据 2011 年人口普查,26 个席位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超过 20%。只有芬奇利和戈尔德斯·格林这样的人可以对犹太人说同样的话。 从历史上看,这也不是常态。阿特金森写道,保守党内部的态度多种多样,从对《贝尔福宣言》的冷漠,到将犹太复国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系起来,再到公开的反犹太主义。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主义倾向在前任和未来的部长中依然强劲,安东尼·纳廷、伊恩·吉尔莫和丹尼斯·沃尔特斯都于 1967 年帮助建立了促进阿拉伯-英国理解委员会。 当然,在 1948 年阿以战争期间,许多托利党人对犹太复国主义怀有敌意,对大卫王酒店爆炸案等暴行感到痛苦,这个时代甚至在当时非常保守的利物浦发生了反犹太骚乱。反对以色列独立运动的外约旦阿拉伯军团由中校约翰·巴格·格鲁布爵士领导。 相比之下,《卫报》在以色列诞生之初就支持以色列,这一举动与其宗教起源有关,该报是由一位神论者创立的,该教派是一个新教教派,在 19 世纪是激烈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曾因否认神性而遭受“犹太化”迫害基督的。如今,《卫报》可能是所有主要英国出版物中最支持巴勒斯坦的,甚至似乎对之前对以色列的支持感到遗憾。 20世纪中叶的一些反犹太复国主义是由上层阶级的偶然反犹太主义推动的,这些人将犹太人视为暴发户,这种观点只是因大屠杀的恐怖而在民众中感到羞耻。 但某些类型的保守党人对阿拉伯文化有着真正的情有独钟。探险家理查德·伯顿 (Richard Burton) 的政治观点将使他在今天被取消,但这位超级语言学家也对阿拉伯文明有着深深的热爱和迷恋。然而,最著名的例子是 TE 劳伦斯,奥威尔将他描述为“也许是最后一个右翼知识分子”。 这并不罕见, 阿里斯·鲁西诺斯最近引用了马丁·艾米斯的回忆录,他在牛津写给家里的信中回忆道,“我昨天遇到了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动派,他支持阿拉伯人对抗以色列”。 还有一些保守党阿拉伯主义者——除了布朗特之外,人们还可能提到艾伦·邓肯、罗里·斯图尔特、德斯蒙德·斯韦恩和尼古拉斯·索姆斯。但他们是一个正在消亡的品种,而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 ——上周日示威活动的发言人——是现代政党的更典型代表。 造成这种下降的一个较小的原因可能是阿拉伯语非常难学,而且像大多数现代语言一样,它的学习也在下降( 我们驻中东的大多数大使甚至都不会说阿拉伯语)。事实上,当今英国最有天赋的保守派知识分子也许是 阿卜杜勒·哈基姆·穆拉德(Abdal Hakim Murad) ,原名蒂莫西·温特(Timothy Winter),在彭布罗克学院获得阿拉伯语双项第一。 但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化,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 阿特金森写道:“正如现代保守党的习惯一样,玛格丽特·撒切尔最改变了该党对以色列的态度。尽管爱德华·希思和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在赎罪日战争期间拒绝武装特拉维夫,但这位芬奇利议员成为第一位访问以色列的英国首相。她将其视为英国在中东最好的冷战盟友。从青少年时期庇护一名奥地利犹太女孩到担任芬奇利议员,撒切尔夫人一生都对犹太人和以色列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与其他许多方式一样,撒切尔夫人让保守党变得更加大西洋化和美国化。 然而美国保守派本身也大幅改变了对中东的立场。 上次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冲突时,我引用了Jeet Heer的一篇文章,他指出美国右派曾经同情巴勒斯坦人,雷格纳里会出版拥护阿拉伯文化的书籍,而 1956 年《国家评论》则称以色列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种族主义国家”。 左翼和右翼互换立场的部分原因是冷战,尽管希尔也认为保守派崇尚力量,并且在 1967 年六日战争取得巨大胜利后,他们对弱犹太国家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也许;左派无疑对受害者身份、非殖民化和种族正义的思想更加感兴趣,常常表现出对残酷暴力和不宽容的解放斗争的喜爱。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也兴起,尽管20世纪初基督徒占巴勒斯坦人口的30%,而且阿拉伯基督徒往往不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福音派人士比美国犹太人更偏向犹太复国主义。 -以色列。一些保守派也受到大屠杀罪恶感和右翼必须摆脱反犹太主义的想法的推动,这就是犹太基督教一词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美国福音派人士总体上往往非常亲犹太人,尽管这种感觉并未得到回报。如今,关于圣地的政治分歧在美国更加明显,民主党选民的同情心发生了巨大转变,在短短 20 年内从对以色列的大约 +35 左右变成了对巴勒斯坦的 +11 左右。 这种对以色列进步观点的转变恰逢“大觉醒”,即在社交媒体和大学的推动下,种族和性别等问题上的观点变得激进。这也部分反映了民主党选民的人口结构变化。 我并不像许多人那样相信我们所看到的学术界对以色列苦难的冷漠是出于对犹太人的仇恨,菲利普·勒莫万(Phillippe Lemoine)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反犹太主义在右翼批评者中更为普遍” 。以色列比以色列的左翼批评者更重要——至少在白人中如此。 在我看来,仇恨以色列的左翼分子较少受到我们传统上理解的反犹太主义的驱使,而更多地受到后殖民理论的驱使,不幸的是,圣地的冲突感觉像是最接近殖民斗争的事情。理论想象它。 保守派越将以色列视为文明国家(即西方国家),我们的反对者就越会通过殖民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这场冲突,这实际上并不公平。以色列存在的最佳论据并不是犹太人曾经拥有这片土地,也不是在欧洲人的种族灭绝手中遭受苦难,而这两者都不是巴勒斯坦人的错,而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此一无所知。逃离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几乎与逃离圣地的阿拉伯人一样多。数百万以色列人是米兹拉希姆人,一直生活在中东。事实上,以色列最大的移民不是来自波兰或罗马尼亚,而是来自伊拉克。 除了看起来明显是欧洲人的德系犹太人之外,以色列的西方游客很难区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如果以色列是一个殖民国家,这些以色列人是否会“回到”一个世纪前三分之一是犹太人的巴格达?说他们没有建国权和安全权是不合理和不人道的。 (我也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权)。 也许,如果没有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那些中东犹太社区可能会继续享受健康的存在,但历史当然没有表明这一点。保守派认为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因此确保一个人生存的唯一方法是建立一个可防御的国家,而不是依赖大多数人或仁慈的统治者的善意——这永远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这种转变也是由阿诺德·克林所谓的文明与野蛮轴心推动的。克林谈到了“政治沟通的三轴模型”,并写道:“进步人士将沿着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轴心进行沟通,并根据(P)二分法来构建问题。”保守派将沿着文明与野蛮的轴心进行交流,用(C)二分法来构建问题。自由主义者会沿着自由与强制的轴心进行交流,用(L)二分法来构建问题。 在圣地,克林写道:“沿着保守的文明-野蛮轴心,焦点是以色列价值观与美国价值观的一致方式。保守派强调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虚无主义。支持以色列就是捍卫文明。支持巴勒斯坦人就是宣扬野蛮行径。沿着进步的压迫者-被压迫轴,焦点是巴勒斯坦人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逆境。进步人士认为以色列的政策对巴勒斯坦的大部分苦难负有责任。支持巴勒斯坦人就是为受压迫的人民挺身而出。支持以色列现行政策就是支持压迫者。” 10 月 7 日之后,这些感觉将得到强烈强化。哈马斯绝对是野蛮的,我脑海中浮现出的类比是青铜时代的袭击或美国西南部的科曼奇袭击。这是发自内心的可怕。 两党制度中的政治分歧往往会加剧,因此一旦一个政党开始主导一个投票人口,其对手就会代表另一个政党。现代右派的大部分定义也是与左派相对立的,而不是具有任何连贯的世界观。 因此,随着工党在一些选区越来越依赖穆斯林选民,保守党也变得更加亲以色列,这一群体拥有数十个席位,在杰里米·科尔宾的统治下最为明显。在上次选举中,英国犹太人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鲍里斯·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而科尔宾则深受其选区北非社区的喜爱,我附近芬斯伯里公园的一家咖啡馆里贴满了科尔宾的照片。 再说一次,这在历史上并不是常态。乔治·伊顿在《新政治家》中写道,“要了解工党与以色列关系的历史复杂性,请回想一下该党的许多左派曾经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1946 年,未来的领导人迈克尔·福特 (Michael Foot) 和未来的《新政治家》编辑理查德·克罗斯曼 (Richard Crossman) 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巴勒斯坦慕尼黑?指责艾德礼政府背叛了犹太国家地位。 直到 1980 年,托尼·本在日记中写道:“我反对巴解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承认,不是因为我反巴勒斯坦,而是因为消灭以色列是巴解组织的目标,而他们与恐怖主义有联系。” .”’ 但此后双方的构成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对于工党来说,圣地的战争可能会令人头疼。超过 300 名穆斯林议员和议员已经写信给凯尔·斯塔默 (Keir Starmer),呼吁停火,而左派 — — 来自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 — 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感情之深不应被低估。激情表达得越多,保守派就越可能感受到对手的疏远。 《历史的错误面》是一本由读者支持的出版物。要接收新帖子并支持我的工作,请考虑成为免费或付费订阅者。
© 2023埃德·韦斯特 |
圣地如何分裂英国
加沙冲突让工党头疼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