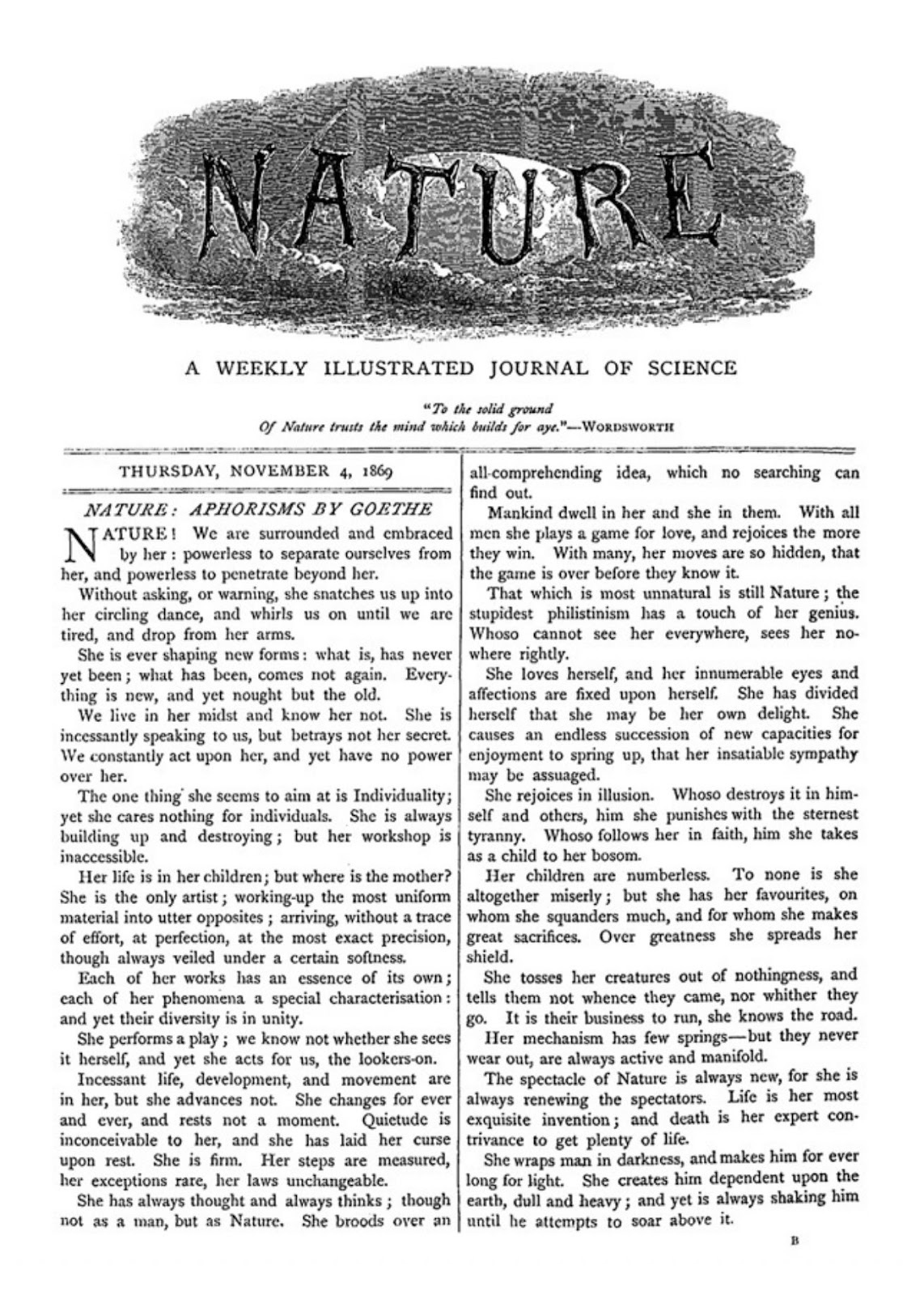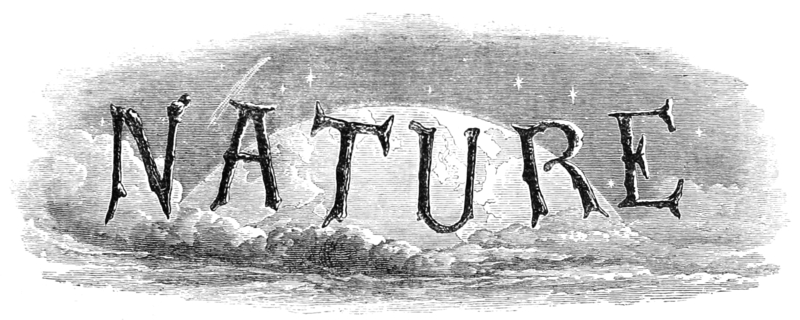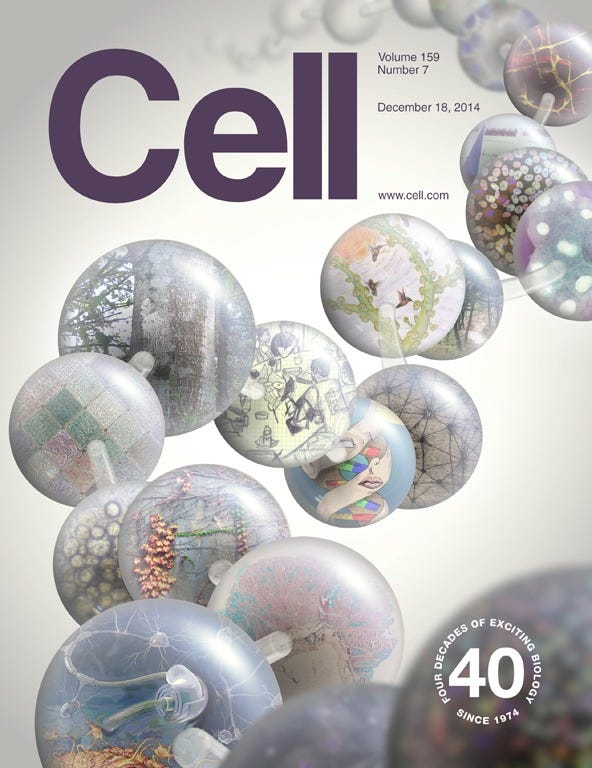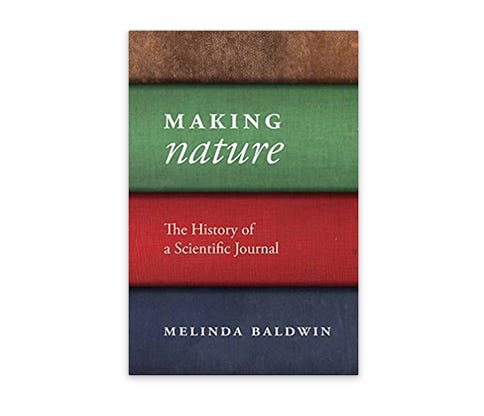【这是2022年书评大赛的决赛选手之一。这不是我的 – 是 ACX 读者在投票完成之前将保持匿名,以防止他们的身份影响您的决定。我将在几个月内每周发布其中一个。当您阅读完所有内容后,我会请您投票选出最喜欢的,所以请记住您喜欢的那些 – SA ]
科学出版的世界是按照地位等级组织的,很像亚伯拉罕宗教中的天使等级。底部是未经同行评审的博客文章和 Twitter 线程。略高于 arXiv 等预印本服务器,然后是PLOS One等大型同行评审期刊。以上是所有特定领域的期刊,有些期刊的声誉高于其他期刊。在顶部,靠近神圣存在的是 CNS 期刊:细胞、自然和科学。
有关基于引文数据的期刊的实际层次结构,请参阅这篇论文,其中将Nature和Science放在首位。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它来自自然出版集团家族的一本期刊。
撇开《细胞》这个更专业的生物学期刊,它似乎进入了中枢神经系统的首字母缩略词,就像 Netflix 进入了 FAANG 的首字母缩略词一样, 《自然》和《科学》非常相似。他们都在所有科学领域发表文章。它们都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它们每周出版一次。他们在 2007 年共同获得了一项对人类服务的大奖。由于他们的巨大声望,让你的论文参与其中是科学家职业生涯中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但是,自然和科学究竟是如何变得如此有声望的呢?这是我希望的问题 科学史学家梅琳达·鲍德温 (Melinda Baldwin) 于 2015 年出版的一本书《创造自然:科学期刊的历史》可能会给出答案。它侧重于Nature ,但考虑到它们的相似性,它的大部分课程很可能可以外推到Science中。
当我意识到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将期刊声望视为理所当然时,我对此产生了好奇。每个人都知道自然和科学非常重要,但很少有人能说出确切的原因。但这很重要!从大学到媒体公司再到大型体育赛事,著名的机构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因出名而出名”之外,了解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很有用。
这比听起来更困难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经常满足于肤浅的答案。例如,选择性是一种常见的解释:声望仅仅来自于获得难以获得的东西,例如哈佛学位、奥运奖牌或诺贝尔奖。 Nature确实有很高的选择性,接受提交的文章不到 10%(绝大多数论文甚至被作者认为不值得提交给Nature )。然而,仅靠严格的选择性并不能解释声望,或者仅仅通过人为设置低接受率来创办一个有声望的期刊或大学将是微不足道的。
另一个简单的解释是长寿。诚然,享有盛誉的机构往往都是老牌的,事实上, 《自然》自 1869 年诞生以来已经存在了 150 多年。科学只是稍微年轻一点,成立于 1880 年。但是有很多更老的科学期刊:最古老的, 《英国皇家学会哲学汇刊》的出版时间比《自然》早 200 年,也就是 1665 年。然后还有更多享有盛誉的近期出版物:例如,《细胞》杂志成立于 1974 年。声望和长寿之间的相关性是真实存在的,但并不完美.它也没有说因果关系:长寿导致声望,还是声望导致长寿?
重要的不是时间本身,而是发生的具体事件——换句话说,就是历史。创造自然,虽然不是专门关于声望的,但正是这样。
我们将首先研究自然的起源以及它如何扰乱当时的出版格局(第一部分)。然后我们将研究使其在其存在的第一个世纪(第二部分)建立声誉的因素。我们将以 1970 年代结束,当时选择性和声望突然对自然和科学出版变得重要(第三部分)。
一、论自然的起源
故事始于Nature的创始人兼第一任编辑 Norman Lockyer。
Lockyer 在英国政府担任公务员,工作轻松,但在业余时间涉足天文学。在 19 世纪,在业余时间涉足天文学可能是一种智力上的爱好:专业和业余科学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即使没有受过正规培训,也不难贡献原创研究。在 1860 年代,洛克耶发表了几篇关于天文观测的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他对太阳的研究中对氦元素的共同发现和命名。他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科学家”(科学家们当时自称)中声名鹊起,很快他就被选入皇家学会。
但天文学是一项开支,而不是收入来源。洛克耶经常通过为非专业读者撰写非专业科学文章和书籍来补充他的政府工作。然后,有一天,他想到了一种新的出版物。这将是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的周刊——但与当时存在的其他期刊不同,它将由杰出的科学界人士自己撰写。它会有一个简单而令人回味的名字:自然。
Lockyer 总结了Nature的两个目标:
第一,将科学工作和科学发现的伟大成果展示在公众面前,并促使科学的主张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得到更普遍的认可;
其次,通过提供世界各地自然知识的任何分支所取得的所有进展的早期信息,并为他们提供讨论不时出现的各种科学问题的机会,从而帮助科学人员自己。
换句话说(并且摆脱了随机形容词和名词的老式大写), Nature旨在做两件事:科学家与公众的交流,以及科学家之间的交流。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这也是一个新的。在那之前,这两个目标是分开的。
回想一下,科学期刊自 1665 年就已经存在。在最初的 200 年里,它们主要用于记录学术团体的会议。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原本就是这样:对皇家学会讨论的任何“哲学”问题的总结。除了期刊,专业书籍很常见,实际上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传播科学的更高地位的方式。查尔斯·达尔文 1859 年出版的《物种起源》是最著名的例子。科学家之间的非正式通信也是一个主要但私人的渠道:达尔文一生写了 15,000 多封信,足以填满 30 卷。
除了一些书籍外,以上都不是为外行准备的。受过教育的非科学家(专业人士、神职人员、政治家等)反而从通才或文学期刊(如 雅典娜杂志。这些出版物中的文章不是由专家撰写的,而是由记者和业余爱好者撰写的。洛克耶与他的亲密支持者托马斯·赫胥黎——一位以捍卫达尔文进化论而闻名的生物学家——分享的观点是,他们充满了错误和神学色彩。他们认为,如果科学家们自己来交流他们的研究,那就更好了。
洛克耶和赫胥黎大胆假设科学家会对从事这种交流工作感兴趣。他们不是。几乎在Nature成立后不久,它的贡献者就忽略了普及部分(鲍德温在书中说,“不是一项高地位的事业”),而是专注于科学内部的交流部分。他们确实按照洛克耶的意图写了自己研究的摘要和摘要,但他们希望他们的读者会是其他科学家。三年之内,作为洛克耶目标受众的受过教育的外行开始抱怨他们无法再理解其中的内容。
因此,大自然的两个目标中的第一个大多以失败告终。幸运的是,第二个目标的意外成功抵消了这一点。
科学家们确实喜欢为洛克耶的杂志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每周出版一次。他们发现在《自然》杂志上撰写自己的研究总结是快速分享他们的结果并获得其他科学家关注的绝佳方式。书很慢;例如,达尔文花了很多年时间撰写和出版《物种起源》 。科学学会的期刊很慢;您必须等待会议召开,然后才能发布会议的“交易”。私人通信很快,但不是公开的。通过出版速度以及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其他因素, 《自然》在生态系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它是 19 世纪英国科学界的推特。
很快,这种模式就被复制了,最著名的是 1880 年的《科学》杂志。据其第一任编辑称,《科学》的明确意图是“在美国,占据‘自然’在英国如此出色的地位”。在短短几年内, 《自然》颠覆了科学出版,并将自己确立为一所有用且独特的科学机构,受到英国和国外专家的认可。
《自然》第一版的第一页,1869 年 11 月 4 日
二、百年信誉
尽管它很受欢迎,但大自然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变得享有盛誉。事实并非如此。 《创造自然》经常提醒我们,该杂志的大部分历史都是低档出版物,只要事实正确,任何东西都可以快速印刷。 (编辑团队的基本检查确保了这一点;直到 1970 年代, 《自然》的文章才得到一致的同行评议。) 直到 1960 年代,一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初步报告的研究人员预计将在“in更严肃的期刊。”换句话说, Nature提供了快速而廉价的分销,而不是奢侈品牌的认可。
正如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中看到的那样,这种情况大约在 50 年前发生了变化。但要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们首先需要检查该期刊从早期到声望接管的大约 100 年期间的特征,从更深入地了解出版速度开始。
出版速度
20 世纪末期《自然》杂志的编辑约翰·马多克斯(John Maddox)说,“《自然》早期最伟大的资产之一就是皇家邮政的速度。”你可以写信给Nature ,一周内发表,两周内阅读对你通讯的回复。这是最先进的通信技术!
考虑一下本书前半部分提到了多少次出版速度(强调我的):
Nature的独特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够充当 . . .通过其通信专栏和每周出版时间表进行讨论。 (第 8 页)
许多英国科学家发现,将科学问题或想法引起研究人员同行注意的最快方法之一就是向Nature发送通信。 (第 39 页)
与文学期刊不同,从投稿到出现在期刊上几乎没有延迟。 (第 63 页)
《自然》杂志的出版速度之所以能吸引科学界人士的第二个原因是,让一个人的作品迅速出版已成为确定科学发现或理论优先级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 (第 65 页)
科学周刊[如Nature ] 在 19 世纪末通过为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可以快速打印短篇文章的论坛,在研究人员的出版策略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第 105 页)
Proceedings [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 和哲学杂志在提交和出版之间都有明显的滞后时间。 . .,这使得《自然》及其每周周转对于注重优先事项的卢瑟福来说具有独特的价值。 (第 109 页)
[卢瑟福] 立即将他最有趣的实验结果 [给《自然》] 发送给了《自然》,这既是为了让他的同事们了解他的工作,又是为了防止像他在 1899 年那样被抢先一步。(第 112 页)
这些引述强调了为什么速度很重要的两个明显原因。第一个,正如我之前所暗示的,是《自然》作为当时学术社交媒体的角色。与私人通信不同,这只是讨论科学主题——或科学本身——的最佳方式,它可以接触到大量受众。下一节将对此进行更多介绍。
第二个原因,正如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提到的那样,是确立优先权。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成为第一个发表新想法或结果的人很重要,但在 19 世纪,这一点不太清楚。再次以达尔文为例,他多年来一直对进化论保密,因为他想在将其提交给公众之前确保他的论点是正确的(尽管他最终确实感觉到了发表该理论的紧迫性)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做到了)。但随着科学变得专业化,“不被挖”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每周的Nature是避免这种情况的好工具。
所有这些关于速度的讨论可能会让最近向《自然》杂志投稿的任何人感到惊讶。 2016 年的一项分析显示, Nature审查一篇论文的中位时间为 150 天,即 5 个月,高于十年前的 85 天。 Nature本身报告说,对于 2020 年,提交和接受之间的中位时间为 226 天。我们距离“不到一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什么出版速度下降了?正如我们所料,原因是Nature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在国际科学界。至少,这是 20 世纪中叶第一次出现放缓的情况。
早期, 《自然》是为英国科学家撰写的期刊。但在 20 世纪上半叶,整个科学,尤其是自然,开始涉及更多跨界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例如,当一个外国政府禁止Nature时,这是一件大事,就像纳粹德国在 1938 年所做的那样;德国研究人员一直将其用作科学新闻的重要来源。该禁令还被《纽约时报》等非英国媒体报道,表明该杂志具有国际新闻价值。国际读者人数的增加意味着向编辑发送了更多的信件和文章,到了 1950 年代,出现了如此多的积压,以至于投稿需要保留六个月或更长时间。
1960 年代,新任编辑约翰·马多克斯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他从清理积压工作开始他的编辑工作,甚至将投稿日期与每篇科学论文一起打印出来,以向每个人展示Nature审稿的速度有多快(“通常在一个月内”,Baldwin 的书说)。显然,马多克斯认为迅速恢复期刊的声誉很重要。有一段时间,他似乎成功了。直到 1989 年,在一场围绕冷聚变的争论中,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说Nature仍然很快:它能够“在短短三周内打印论文,而不是通常的 6 到 12 个月其他科学出版物。”
因此,尽管由于其受欢迎程度和国际影响力在本世纪中叶有所下降,但快速出版仍然是 1970 年代《自然》杂志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二次——迄今为止是永久性的——下降发生在最近,可能是由于声望和近乎即时的在线平台的竞争,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网络效应
截至 2022 年,科学家们在 Twitter、博客和其他在线平台(如ResearchHub )上公开争论。在 19 世纪,还没有发明 Twitter 和 ResearchHub [需要引用]。幸运的是,大自然在那里。
当产品的价值主要来自使用它的人时,就会出现网络效应。如果有两个相互竞争的电话系统,最有价值的一个是拥有最多用户(或至少是您想与之交谈的用户)的那个。如果你创建了一个改进的 Twitter 克隆,那么如果你不能以某种方式设法捕获 Twitter 的数百万人网络,那么它所有令人惊叹的功能将无济于事。同样, 《自然》成为一本值得阅读和投稿的有趣期刊,因为它获得了英国科学精英的关注,成为讨论重大科学问题的场所。
作为论坛的角色在《自然》的历史上一直存在,正如《Making Nature》节目中对发生在期刊页面内的辩论的详细叙述。一些例子:
-
关于 1880 年代地球年龄的争论。
-
1920 年代的辩论 关于科学家这个词是否可以用来描述从事科学的人而不是科学人或科学工作者。
-
1950 年代和 60 年代板块构造理论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和科学几乎处于同等地位)。
-
1980 年代关于顺势疗法和冷核聚变的备受瞩目的争议。
Nature是如何成为英国乃至世界的主要科学论坛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每周发布时间表是关键因素之一,因为讨论需要人们能够及时相互回复。但仅靠速度是不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有许多科学周刊, 《自然》甚至都不是最受欢迎的:在 1870 年代,“其他周刊——如化学新闻、知识和英国机械师——都拥有比《自然》估计的 5,000 多的订阅者。 ”为什么这些杂志中没有一本成为讨论科学的最佳场所?
一个答案似乎是,诺曼·洛克耶个人喜欢争论,并在他的日记中鼓励“激烈的分歧”,这使它成为渴望就科学思想进行斗争的人的理想选择。如果洛克耶选择缓和他收到的一些致编辑的信的语气,甚至拒绝出版,那么辩论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很容易与今天蓬勃发展的社交媒体相提并论,我们也将礼貌地称之为“激烈的分歧”。
另一个答案是, 《自然》设法在通才和专业出版物之间的权衡曲线上占据了最佳位置。由于涵盖了所有科学领域, 《自然》比《化学新闻》这样的杂志更适合讨论跨学科问题以及应该如何进行科学的问题。同时,就其受众和撰稿人而言,它是一本专业期刊:他们几乎都是专业科学家。再加上英国的大多数科学家以及相当大比例的非英国科学家都阅读了它的事实,你会得到一份被广泛认为是“找到合适的人”作为化学编辑的最佳方式的出版物新闻本人在 1895 年承认。
建立这个“合适的人”网络是洛克耶从一开始就明确的目标。创办期刊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科学界人士——有些是他个人认识的,有些是他的名声认识的”(即他冷冷地给他们发电子邮件),将他们的名字公开为支持者和未来的贡献者。这些名字中最重要的是前面提到的托马斯·赫胥黎,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也是文学期刊上的流行散文家,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团体 X 俱乐部的领导者。赫胥黎是洛克耶项目的坚定支持者,早年他经常为《自然》撰稿,这有助于巩固其声誉。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受欢迎的科学家——是的,我又在谈论达尔文了——也喜欢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达尔文在该杂志创刊时已是一位年迈且备受尊敬的科学家,他经常寄给洛克耶的刊物的摘要和信件无疑提升了该刊物的地位。
而这只是一长串家喻户晓的名字的开始,他们曾或多或少地与大自然接触过。例如,在物理学中,开尔文勋爵、欧内斯特·卢瑟福、尼尔斯·玻尔、恩里科·费米和莉丝·迈特纳都是重要的贡献者。该领域的一些最著名的论文,例如詹姆斯查德威克 1932 年关于中子可能存在的报告,或梅特纳和奥托弗里施 1939 年提出核裂变想法的信函,都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在生物学方面,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 1953 年关于DNA 结构的研究可能是其页面中出现的最具历史意义的论文。
由于自然在 20 世纪中叶很受欢迎,但仍然不是很有声望,我很乐意假设这些著名的科学家和发现有助于它的声誉,而不是相反。今天,因果关系的箭头大多是颠倒的:科学家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他们在最负盛名的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而不是期刊因为发表大牌和大论文而变得有声望。当然,由于网络效应,这是一个不断造福自然的自我强化反馈循环。
最后,谈谈语言。 Nature显然是用英文出版的。但早在 19 世纪,英语并不是主要的知识语言:法语和德语更为重要。由于大英帝国和美国的政治主导地位,英语作为科学语言的兴起发生在 20 世纪。因此, Nature及其在美国的同类Science相对于法国(例如La Nature )和德国(例如Naturwissenschaften )同行获得了重大优势。
创造自然并没有强调这一不言而喻的观点,但值得一提的是,自然受益于全球网络效应,这种效应在盎格鲁圈之外是难以实现的。
生存与保守主义
速度、精英网络和英语很棒,但如果您的出版物未能盈利并关闭,它们将无济于事。正如他们所说,幸存者偏见的教训是,你应该优化成为幸存者。因此,与大多数同时代人不同,自然的故事也是它如何设法生存的故事。
Nature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家名为 Macmillan and Company 的伦敦出版商的合资企业。它的目的是赚钱。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一个拥挤的期刊市场。在证明无法吸引足够的订阅者之后,出版物通常只持续几年。 Lockyer 本人曾作为联合创始人和科学编辑短暂参与过名为The Reader的通才杂志,该杂志仅存在于 1863 年至 1867 年(并在 1865 年失去了科学版块)。将其与Nature广受欢迎的成功进行对比会很诱人,但正如我们所见, Nature的大多数目标读者甚至无法理解该期刊,因此其订阅者基础和收入仍然很小。
因此,大自然的生存取决于其所有者亚历山大·麦克米伦的善意。这需要很多善意!自然亏本经营了整整 30 年。直到 19 世纪末,它才开始盈利。
这种对经济损失的惊人容忍似乎源于麦克米伦公司的其他活动:他们出售科学书籍,而《自然》是进入该市场的好方法。尽管如此,如果没有一位富有的出版商长期致力于支持洛克耶的项目,它很可能无法幸免于难。
Lockyer 也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承诺。从 1869 年到 1919 年,他担任该杂志的掌舵人整整半个世纪。尽管他的继任者中没有一个人能担任这么久的职位,但大多数人至少会持续 20 年,导致八位编辑的名单非常短—— 153 年的历史。与此同时,该杂志从未出售:麦克米伦公司仍然存在,并且仍然拥有Nature ,尽管公司合并使得确切的所有权结构难以弄清楚。 ( Springer Nature是一家于 2015 年通过合并 Macmillan 的一些部门和其他实体而创建的公司,是Nature的直接母公司。)
出现的画面是一个稳定、保守的机构,拥有忠诚的所有者和编辑,尽管它见证了科学本身的变化,但它变化缓慢。
这很好地反映在Nature的使命和视觉识别的稳定性上。最初的使命宣言从 1869 年到 2000 年保持不变,包括对“科学家”和“科学界杰出人士”的性别引用。 当前版本较短且不分性别,但总体相似,尽管我注意到两个主要目标的顺序已经颠倒:
首先,通过及时发表任何科学分支的重大进展来为科学家服务,并为报道和讨论有关科学的新闻和问题提供一个论坛。
第二,确保科学成果迅速传播给全世界的公众,传达科学成果对知识、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同样,最初的刊头图片可以追溯到第一期,在该期刊的顶部出现了 89 年,直到 1958 年(略有不同)。
创造自然的一个中心点是自然与英国和国际科学机构共同进化。为此,它必须在保守主义和创新之间取得平衡。我的印象是,大自然更多地处于保守的一端,是其他科学可以发生的坚如磐石的舞台。
这种态度从一开始就很有帮助,但在 1970 年代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它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三、 WTF 发生在 1970 年代?
来自社会科学的一个有趣的谜题:七十年代初发生了什么?从大量图表可以看出,1971 年左右社会的各种模式似乎已经偏离轨道,包括工资增长、通货膨胀、住房成本、能源消耗、律师人数、离婚率、生育率和肉类消费。无论是巧合还是同一神秘现象的一部分,我们都可以在此列表中添加科学出版业声望的上升。
需要明确的是,我是声称这种转变是一个具体而重大的事件的人。梅琳达·鲍德温(Melinda Baldwin)多次承认, 《自然》杂志从低档杂志变成了有声望的期刊,但她对于究竟是什么转折点仍然含糊其辞。在关于 1970 年代的章节中,她将增加的选择性和声誉视为这一时期发生的许多事情之一。直到在写这篇评论的过程中——故意关注声望——我才意识到在那十年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而且这件事影响的不仅仅是自然。
让我们看看这本书确实告诉了我们什么,然后我将从其他地方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1970 年代自然的变化
1970 年代与《自然》最短任期的编辑大卫戴维斯的领导相吻合。戴维斯于 1973 年从约翰·马多克斯手中接过职务,并着手进行了一些改变。在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实验后,他再次将《自然》杂志制作为单一出版物,将其分成三个期刊。他改革了贡献者的风格指南。他允许在他的社论中使用卡通和幽默。他还彻底改变了期刊的外观:从现在开始, Nature的封面将采用有趣的图像,而不是文章或广告。
今天的封面仍然是这个传统。这是 2016 年的Nature封面,用于该期刊的 Wikipedia 页面。
Maddox 和 Davies 领导下的Nature遵循与过去几十年相同的国际化趋势,但 70 年代可能是英国以外增长最快的。考虑一下这些关于编辑人员变动年份的研究文章来源的近似统计数据:
-
1966 年(Maddox 成为编辑时):40% 来自英国,60% 来自国际
-
1973 年(戴维斯):33% 来自英国,67% 来自国际
-
1980 年(又是马多克斯):20% 来自英国,80% 来自国际。
当然,“国际”主要是指美国。 1960 年代和 70 年代是美国在包括科学在内的大多数领域超越所有其他国家的黄金时期。自然不能忽视这一点,并于 1970 年在华盛顿特区开设了一个卫星办公室。然而,有趣的是,该杂志的英国性似乎帮助它被视为比其竞争对手《科学》更国际化,法国、德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国家可能认为太美国化了。
几十年前, 《自然》的国际发展放缓了其出版速度。但这一次,马多克斯和戴维斯致力于快节奏。必须牺牲其他东西。结果是接受率急剧下降:“1974 年, Nature印刷了大约 35% 的提交论文;到 1980 年代末,接受率将降至 8 篇论文中的 1 篇,即 12.5%”正如鲍德温所说,这意味着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被视为科学成功的标志”——唯一提及声望的在整个章节中。
1970 年代也是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某些做法变得普遍的时候。同行评议,现在被认为是科学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那时才在自然杂志上系统化。此前,编辑保留接受或拒绝任何投稿的权利,只有在其他研究人员认为自己没有必要的知识时才要求他们提供反馈。
另一个新的发展是期刊绩效指标——我的意思主要是影响因子。影响因子是期刊重要性的代表。 It is calculated from the number of times the journal’s articles from the last two years were cited across al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the idea being that more commonly cited works are more impactful.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list of impact factors was published in 1975: that year, Nature was ranked 109th out of all journals in the list. But within five years, in the 1980 rankings, Nature had risen to the 49th position. Today it usually ranks first on most measures of impact .
The impact factor and related metrics are widely seen as problematic for many reasons, but they certainly do show that Nature ’s reputation rose in the 1970s. It also seems obvious that their very invention contributed to the shift towards the prestige economy we see today: before sending work to a journal, a researcher can now look up the rankings and pick the most “impactful” journal that is likely to accept the submission. But Making Nature doesn’t discuss this. Nor does it describe what happened in the rest of academic publishing at the time, such as the rise of another prestigious journal: Cell .
A Tale of Two Disruptions
Remember when, in the introduction, I suggested that the journal Cell might be less deserving of its inclusion in the CNS acronym than Nature and Science ? Well, I may have to take it back.
Making Nature does not mention Cell , except a few times to identify it as a rival to the other two. But as I was pondering the shift to the prestige economy in science, I remembered reading an in-depth 2017 article from The Guardian that did talk about Cell in the wider context of scientific publishing. Here’s the relevant part (emphasis mine):
“At the start of my career, nobody took much notice of where you published, and then everything changed in 1974 with Cell ,” Randy Schekman, the Berkeley molecular biologist and Nobel prize winner, told me. . . . [ Cell ] was edited by a young biologist named Ben Lewin, who approached his work with an intense, almost literary bent. Lewin prized long, rigorous papers that answered big questions – often representing years of research that would have yielded multiple papers in other venues – and, breaking with the idea that journals were passive instruments to communicate science, he rejected far more papers than he published .
What he created was a venue for scientific blockbusters, and scientists began shaping their work on his terms. “Lewin was clever. He realised scientists are very vain, and wanted to be part of this selective members club ; Cell was ‘it’, and you had to get your paper in there,” Schekman said.
Notice the timing: Cell was founded in 1974,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as metrics like impact factors became widespread, and right before Nature ’s acceptance rate started to plummet.
This suggests that the primacy of prestige in science publishing was not a vague tren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20th century. It was tied to a specific event of the mid-1970s: the invention of a new style of journal. “Suddenly,” the Guardian piece continues, “ where you published became immensely important. . . . Almost overnight, a new currency of prestige had been created in the scientific world.”
Cell and other journals by its parent company, Cell Press, tend to have amazingly aesthetic covers. That seems consistent with positioning as a luxury brand.
Other publications, old and new, tried to replicate Cell ’s success. The Guardian article focuses on British tycoon Robert Maxwell, who took advantage of the shift to expand Pergamon Press, a media empire built out of scientific journals. But by triangulating between that article and Melinda Baldwin’s book, we can conclude that no publications were better positioned than a couple of well-known, fast-paced, generalist, English-language journals: Nature and Science . “Suddenly,” “almost overnight,” there was a prestige game — and they won it.
And whether the timing is a coincidence or not, the invention of impact factors around then probably accelerated the trend. Games need clear winners and losers, and journal impact rankings provide exactly that.
Why doesn’t Making Nature talk about this? One possibility is that the Guardian article is mistaken or exaggerated. Surprisingly, this was difficult to fact-check: I googled around and didn’t really find any other references to Cell having had such a transformative effect on scientific publishing. It could mean that the real effect wasn’t that dramatic — or it could mean that Cell ’s impact has been overlooked. I’m tempted to believe the latter, since I otherwise don’t know of a good explanation for Cell ’s considerable prestige.
If the Guardian piece is correct, then it sounds like there’s a blind spot in most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prestige, even Melinda Baldwin’s. That may be because it’s easier to assume journal prestige was an inevitable trend. A narrative like this one seems superficially plausible: as science became truly global and performed by an ever growing number of researchers, journals had to become more selective, and increasingly provided a useful (and scalable) signal to distinguish the best scientists from the rest. This hypothesis is probably true to some extent,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s no strong reason that journals — and even more so, specific journals — have to provide this signal. Scientific prestige managed to exist just fine for centuries without being tied to the periodical your work was published in.
So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suppose that Nature ’s success was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a general theory of prestige. The specific details matter. And in this story, the details include the invention of not one but two disruptive styles of journal: one in 1869, with a focus on speed, and one in 1974, with a focus on selectivity.
Making Nature ’s biggest weakness, then, would be in not recognizing the existence of this second disruption. It isn’t a unique failing: Nature itself, in the history of the journal published on its website, says nothing about prestige or reputation in the 1970s. Perhaps it would have been gauche to do so. Yet it seems clear that the story of Nature (and, I assume, Science ) is incomplete without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ever the f*** happened in the 1970s.
结论
Let’s summarize Nature ’s rise to fame. It began 153 years ago as an experiment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e experiment failed at its primary aim, but it lucked into a useful niche: fast communication between men of science across disciplines. This allowed it to build a network of elite scientists and a venue for scientific debate. All of this was possible thanks to the editorial commitment of Norman Lockyer and the financial commitment of Macmillan and Company. Fast forward a hundred years, and suddenly (perhaps because of Cell ) scientists start caring very much about where their papers are published. Nature , alongside its twin Science , is propelled to the top of the new prestige hierarchy.
The story told in Making Nature doesn’t stop there. There is a chapter on the 1980s that shows how deft the journal was at managing controversies over homeopathy and cold fusion, two events that reinforced its status as a guardian of “proper” science. Then, in the conclusion, Melinda Baldwin gets into the recent history of Nature , which involves a third important disruption of scientific publishing: the advent of the web.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e web has profoundly changed the way scientists interact with scientific results. But interestingly, the instantaneousness of online publication — whether on blogs, in the comments below an article, in social media, or on a preprint server like arXiv and bioRxiv — hasn’t affected Nature very much. We might have naïvely expected that it would have tried to keep up with the new platforms, since speed was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 But it didn’t. And that hasn’t made it obsolete, either.
This is the strength of prestige. Once it’s established, it becomes a self-sustaining loop. Any useful attributes that helped jump-start the loop, like speed of publication, end up mattering much less.
And then, when the prestige loop is running at full throttle, you get something like the current state of academic publishing: a system that many researchers feel is broken in multiple ways, but which feels impossible to change because of the powerful incentives in place.
Yet there is a glimmer of hope. Studying Nature ’s history made me realize that the institutions of science are not static or eternal. The prestige associated with Nature and Science matters a lot now , but that has been true for only fifty years — not such a long time in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So there’s no reason that we can’t reform the angelic hierarchy of scientific publishing, if we want to. We just have to know what we’re up against. With satisfying depth and crisp writing, Making Nature provides the account we needed of one of the top institutions of science. This is crucial stuff for anyone who wants to understand how they work, or who would set to the task of creating new ones.
原文: https://astralcodexten.substack.com/p/your-book-review-making-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