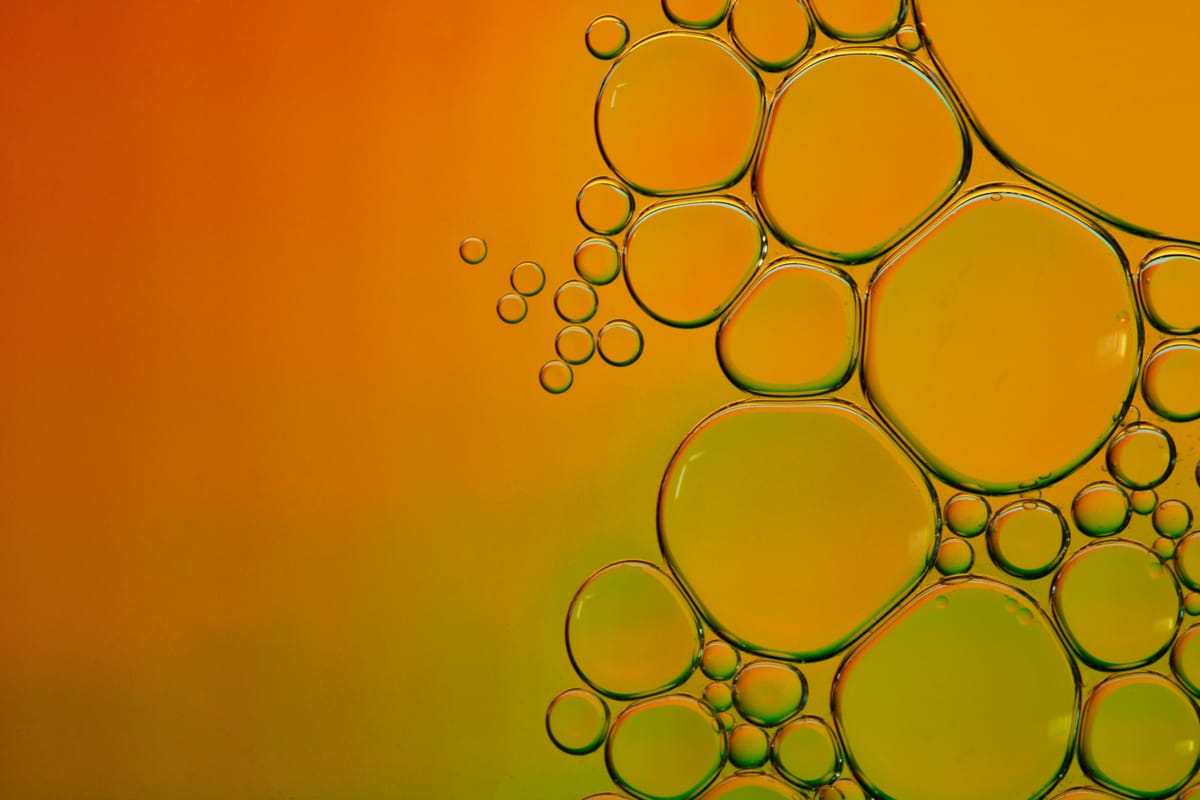
如果你听过这个,请阻止我:想象一个人们的意识一分为二的世界。
每天两次,他们跨越各自部分之间无形的鸿沟,首先作为一个部分生活(我们称之为“Outie”),然后作为另一部分生活(我们可以说,“Innie”)。
Outie 存在于正常的外部世界,而 Innie 则生活在他们无法真正逃脱的受限现实中。
视角切换的一刹那,两人都记不清对方经历了什么。
显然,我正在描述非常受欢迎的电视节目《遣散费》 ,但我想说的是,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这也适用于我们醒着和睡着的自己。我半认真地认为我们应该想知道:我们是否有可能正在折磨我们的内向者?
想想一个永远记不起自己梦想的人。他们知道在过去的八个小时里他们一直处于某种状态,并且有一些经历。但他们不知道这些经历是什么。他们告诉自己,梦中的自己可能很快乐,可能有美好的梦想和有趣的经历。尽管如此,他们时常会带着一种奇怪的不祥预感醒来,就好像刚刚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他们不记得那是什么。
我们清醒的自我和梦中的自我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塞弗伦斯的外向者和内向者之间的关系。
有一些相似之处——双方都不能完全记住另一方的经历,但有一些跨越界限的情绪流淌。
当然,两半之间存在一些权力不平衡:Outie 首先决定接受意识分裂程序,而 Innie 则必须承受后果。
我实际上不确定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给我们的睡眠带来更好的体验。但我确信我的 Outie 和 Innie 的健康之间存在权衡。例如,如果我从事一份有压力但高薪的工作,我的Outie可以享受更多的金钱和资源,但我的Innie只是承受压力而没有任何好处。
仅仅因为一份有压力的工作可能会导致我梦想中的不公平的不快乐,就很难辞掉它。但是,如果我确信我梦想中的自己(内妮)正在为一些只对我的外向有利的事情而受苦呢?我是否能够为了一个我从未真正见过的梦中自我的利益而伤害自己?
道德哲学的基石之一是,一个人可能会在自己内心做出权衡——接受一些伤害来换取一些补偿性的好处——而为了给自己谋取利益而对未经同意的陌生人施加同样的伤害是不道德的。
例如,对我来说,进行一种感觉就像被打在脸上的锻炼是完全道德的,因为对健康的好处对我来说是值得的;对我来说,随意打陌生人的脸是不道德的,尽管这也可能有助于我保持体形。
当两个实体在相关意义上是否是独立的道德主体含糊不清时,就会出现棘手的道德问题:
- 有些人和文化将孩子和父母视为独立的道德主体,因此父母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孩子,而另一些人则将家庭视为一个道德单位
- 许多人对犯罪和惩罚的直觉部分取决于个人身份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足够的变化,以至于我们错误地惩罚了一个与最初犯下错误的“同一个人”不同的人。正如雷德在《肖申克的救赎》中所说:“那个孩子早已不在了,只剩下了这个老人”
- 很多人都在纠结如何对待他人在毒品或酒精影响下的行为:一方面我们必须让人们对他们在醉酒昏迷时所做的事情负责,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毒品或酒精会让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 (此外,在第三种意义上,如果一个人没有有意选择喝醉或吸毒,例如,如果他们的饮料被掺入了药物,那么道德责任就会发生变化)。
在这个清单中,我想添加“我们梦想中的自我的道德权利”;我尝试进行文献综述,发现没有任何人谈论这一点的例子,但道德考虑的范围不断扩大,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虽然我找不到任何人讨论梦想家的权利,但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显然就接受麻醉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据我了解,医学上对麻醉的理解是,病人感觉不到疼痛,不留下任何记忆。但布鲁姆从哲学角度问道:如果一些患者(处于麻醉状态)感到异常疼痛,然后当他们回到清醒意识时这些记忆被抹去怎么办?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会更好:至少这样受苦的人就是受益的人。目前有一个单独的人短暂地存在,受到折磨,然后再次突然消失。也许我们做梦的自己也是如此,尽管目前还不清楚我们能做些什么。